崖丽娟诗评 | 凌越:诗人的责任在于给本民族语言带来活力
诗人的责任在于给本民族语言带来活力 ——凌越诗集《飘浮的地址》读后 崖丽娟 诗集《飘浮的地址》是诗人、译者、评论家凌越近十年精品佳作的结集,代表其迄今为止诗歌创作的高峰。我研读了三遍才有如此浅见,第一遍是在2021年7月24日凌越从广州来到上海民生美术馆参加“诗歌来到美术馆”分享活动,第二遍是在2022年3月21日“世界诗歌日”前夕,应“澎湃新闻”之邀做凌越的访谈,第三遍是在访谈结束后不久萌生写一篇浅评的想法。试图通过分析他的文本来印证他在访谈时阐释的诗学观点,毫不夸张地说,反复研读不仅充分领略到凌越如何用庞杂诡异的意象和惊人的想象力表达他对当下、对历史的反思和追问,而且透过其智慧洞见出非同一般的诗意人生。 一、宽阔的自然与人文视野,以《暴风雨》为例 凌越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评论家、译者。像他这样综合素质全面的诗人,对写下的文字要求非常高,甚至用挑剔来形容也不为过。他对诗歌语言艺术的孜孜追求和取得的卓越成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博尔赫斯对“诗歌的任务”有两点看法:一是,传达精准的事实,二是,像近在咫尺的大海一样给我们实际的触动。读凌越的诗,我的深切感受便是他竟然如此精准地传达了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感受与认知,同时又神奇地将读者带入他所观察的情境、事境、物境,感同身受地掀起情感的波澜,内心风起云涌般树欲静而风不止,引人遐思,欲罢不能。且看诗集的第一首诗《暴风雨》: 暴风雨,被深埋的心狂野的饰物, 标明失窃的土地。 暴风雨,在你伟力的驱使下,往昔在皲裂。 多么丑陋的沟壑, 别想阻拦暴风雨的急行军。 暴风雨,对准呼救的窗户, 请释放你的雷霆。 人影在闪烁,有人大笑,有人诅咒。 暴风雨,言语失禁,倾泻而下。 去洗刷瑟瑟发抖的屋顶, 去洗刷人的胆怯和卑微。 老国王,我和你一样还有一颗不甘堕落的心。 暴风雨,一根闪电 在你的痛哭中欢快地舞蹈, 在你的灰幕中疾进的闪电多畅快。 把大地碾为灰烬吧,戕害与被戕害的被祝福。 这首诗多次重复的“暴风雨”不仅强调了它的威力,而且增加了语言的节奏和张力,表达诗人内心强烈的情感,他以词语之珠串起丰富的意象重塑平白无奇的现实世界,关注内心、关注当下生活。作为一个清醒而自觉的人,“我和你一样还有一颗不甘堕落的心”。诗人竟然像“一根闪电”一样“在你的痛哭中欢快地舞蹈,/在你的灰幕中疾进的闪电多畅快。/把大地碾为灰烬吧,戕害与被戕害的被祝福。”通过对大自然现象细致入微的观察从而获得精神层面的体悟,这种宽阔的自然与人文视野,超越了一般诗人的自怜自爱、孤芳自赏,读者由此领受了作者的深刻哲思与诗歌的深邃意涵。这种由大自然静谧的观察演变成人文精神的诗意倾泻,在诗集中《闷热的夏夜》一诗里有同样精彩的表述:“繁星的朗读声,/合拢在纸页的黑暗里。/诗句的引擎,拽着你在时空里任意穿梭。//时钟滔滔不绝的倾诉,/被夏夜的逗号阻止,少年噤声——/阅读葆有泪水的清澈和圆满。” 凌越将自然与人文巧妙结合使语言的内涵与外延获得尽可能丰富的边界,也使诗句获得足够的感染力与爆发力。诗人具有非常扎实的文字功底,此诗文字精准、语意练达、内蕴丰盈。 二、历史省察与语言警醒,以《开往辛亥年的火车》为例 凌越的诗歌有着崇高的历史意识,在《开往辛亥年的火车》这首诗中表达出这种独特的思考认知,诗人大胆展开各种联想,情绪高涨带着自己和读者乘上这辆“开往辛亥年的火车”,自如地穿梭于历史隧道与现实场景之中,将110多年前那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中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诗意地还原于眼前。全诗有6节52行,在此引述其中的3节。 我是开往辛亥年的火车, 我在大地上粗野地漫游, 我代替疯狂扭动的百万条舌头在低吼。 我运载着士兵、商贾和官吏, 我把历史引入动荡和血腥的窄轨。 我在张灯结彩的正阳门车站目睹刺杀的爆炸, 我看见瘦小的官员倒伏在检票处旁的铁椅子上。 …… …… 我是开往辛亥年的火车, 我在咨议局热烈的争论中穿行, 我在死亡虚幻的激情中穿行。 我看见一张张麻木的被蹂躏过的脸庞, 我看见革命党人在呐喊,但听不见声音, 我看见总督府门前人民被排枪击毙,尸体累累。 我继续在上天的滂沱泪雨中穿行, 道路多么遥远而艰辛啊, 我是一个新手,但我有鲁莽的决不妥协的气质。 …… 我是开往辛亥年的火车, 我带着你从第一道曙光里醒来, 我热爱你懵懂的表情里隐藏的热烈, 我和你同样来自大地,在大地上工作、磨练。 我是开往辛亥年的火车,我也是那个勇敢的人, 请拉响尖锐的汽笛—— 请和我一起呜咽、低吼和咆哮, 尽管悲伤,请和我一起找寻没有杀戮和谎言的国度。 我是开往辛亥年的火车,我是道路,我是人。 以上是该诗的第一、四、六节,诗人仅仅用了52行诗就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浓缩并进行深刻反思:“请拉响尖锐的汽笛——/请和我一起呜咽、低吼和咆哮,/尽管悲伤,请和我一起找寻没有杀戮和谎言的国度。/我是开往辛亥年的火车,我是道路,我是人。”这种非同一般开阔、高远的创作视野,展现了深邃的历史眼光与悲悯情怀,其饱满的情感通过叙事描述,以恰当的语言形式精准地传达思想意识,超现实的意象背后,是作者的骨气和脾性,有着他对改变中国命运的这场惊天动地的历史变革独特思考,透过这样真诚的诗句,读者感受到他的体温与呼吸,他的爱恨与褒贬,触摸到作者那颗跳动着的炽热的心。读来酣畅淋漓、令人快意振奋。 行文自此,自然而言联想到对凌越访谈时,他在回答如何写好诗与做好诗歌批评时,做了如此表述:“诗歌史的慢慢延长,使诗人必须要有一种历史意识,他需要了解诗歌史上诗人们各种不同的写作路径和写作策略,并以此为依据在自己的时代决定自己所需要采取的路径。因此现代诗人通常有一种分裂倾向,一方面他是那个被激情所驱使的诗人,一方面另有一个冷静的他者在一旁打量这一切,并帮助那个激情的诗人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以保证诗句本身达到最优效果。”印证了凌越在创作时对历史的自省与对语言的警醒,正是这种高度的自觉使他写出一首首出色的诗。 《开往辛亥年的火车》的意义还在于它回应了新诗被诟病的一个缺陷,即新诗对思想情感与语言的锤炼不足。“我在大地上粗野地漫游,/我代替疯狂扭动的百万条舌头在低吼”、“我在咨议局热烈的争论中穿行,/我在死亡虚幻的激情中穿行”、“我继续在上天的滂沱泪雨中穿行,/道路多么遥远而艰辛啊,/我是一个新手,但我有鲁莽的决不妥协的气质。”这些诗句不仅思想情感鲜明,而且语言高度凝练,从思想到表达都不需要重新“翻译”的环节,思想的媒介与表达的媒介也不存在需要逾越的沟壑。正如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指出:“语言的锤炼必定同时是思想情感的锤炼,锤炼语言的形式技巧也必定同时是锤炼思想情感的形式技巧”(参见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三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诗人写的是历史,语感却非常现代,语言与思想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这显示了凌越在题材开掘、视角选择、语言淬炼、意象捕捉、表述方式等方面的卓越能力。 这样优秀的诗作还有《题一帧照片》,“对岸的楼宇静静矗立,/一股浓烟从金融区中心地带升起,/像肮脏的画笔,/涂染着九月深邃的蓝天。//当飞机撞向塔楼时,/五位青年也曾站起,手搭凉棚/朝曼哈顿方向张望。/现在他们安静下来,继续刚才有趣的话题。”通过一帧已成为历史资料的照片来再现现场情景,传达出诗人对于恐怖事件的强烈谴责和对于和平的珍爱与维护,语言相当警醒与自觉。《马西亚斯,吹起你尖锐的长笛》《马雅科夫斯基在特维尔大街普希金纪念碑前》《我喜欢荒凉的东普鲁士平原》等等都体现出诗人的崇高历史意识与悲悯情怀。 以历史为创作题材的诗作,从不同角度表达深邃的意境,充分显示诗人的格局、眼界和笔下功夫,这些力透纸背的诗句,血性与柔情并存,诗人游走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用语言切分组装成奇妙的世界,浑然一体,令人叹服。 三、自我诗学追求与诗意生活态度,以《青砖宿舍楼间的草坪绿如梦境》为例 如果把凌越看作是仅仅擅长抒写“大诗”的诗人也失于片面,他的一些“小诗”相当精致、澄明、优雅、隽永,如《眺望》“山因眺望而隆起,/水因眺望而远流。//夜因眺望而闪烁,/词因眺望而静默。//白云跨越山峰,/追赶高飞的鸟群。//雷霆在头顶滚动,/秋菊在大地的祭坛上燃烧。//从冰冷的黄昏不经意传来轻蔑的笑声,/——是起身告别的时刻了。//黯淡的星宿,恍惚的树林,/在我身上苏醒。”一个热爱生活、剔除杂念、坦率真诚的人,才会有这样明亮、澄澈的眼睛,无论现实生活多么喧嚣与浮躁,诗人专注于对诗意的创造“词因眺望而静默”,写出清心之诗、轻盈之诗、隽永之诗。凌越在诗歌这条孤独的道路上默默踟蹰于自我诗学追求与精神世界的锤炼,低调、沉稳、洒脱却无比的清醒、自信、坚定。诗意地抵御庸常生活,审视自我的精神,用诗歌寻找自我存在。读他的《青砖宿舍楼间的草坪绿如梦境》,仿佛看到他在华东政法大学读书的青春岁月,这首诗是诗人毕业多年后重返华政校园写下的。 青砖宿舍楼间的草坪绿如梦境, 冷雨中,紫藤开得正艳。 空气里不再有苏州河水腥臭的味道, 校园桥上,两个女生谈论着淘宝。 仅仅像是从一场睡梦中苏醒, 而我丢失了二十年的光阴。 灰色苍穹斜睨着眼, 看不上那一点微不足道的感慨。 有人在楼道尽头笨拙地拨弄吉他琴弦, 校园里的青春烦闷无比。 当我重返这座当年美丽的囚笼, 苔藓如地毯铺展到胸口。 与同学离别的依依惜别仿佛还在眼前,毕业多年后重返校园触景生情,凌越生发出一份深切的怀念,读者能从中感受到那份情意,联想到自己曾经相似的经历,从而引起情感共鸣。诗中虽然有淡淡伤感:“仅像是从一场睡梦中苏醒,/而我丢失了二十年的光阴。/灰色苍穹斜睨着眼,/看不上那一点微不足道的感慨。”满溢的却是温馨、温暖和温柔:“当我重返这座当年美丽的囚笼,/苔藓如地毯铺展到胸口。”校园怀旧诗从题材来看并不新颖,从中却透露出诗人的纯真与深情。凌越1989年从安徽铜陵考到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就读,在当时与居于上海的诗人陈东东、肖开愚、宋琳、朱朱等有过频繁接触、交往,自此有意识地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自觉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从大学校园成长起来的诗人,这样的生活经历自然是令人怀念的,诗人是念旧、珍惜友情之人。从中不难理解这首诗中诗人所倾注的情感。美国诗人庞德有一首写罗马的诗:“呵,初到罗马来寻觅罗马的游人/,你会发现罗马找不到能够称为罗马的东西/那些断垣颓壁和宫殿的旧苑荒台/,罗马的名称只能在这些院墙之内保留/。瞧一瞧兴衰荣辱是如何发生的吧/。她曾经迫使全世界俯伏在她的法令之下/,征服了一切,如今却被征服/,因为她是时间的牺牲品,而时间荡尽了一切”。对于庞德而言“时间荡尽了一切”,对于凌越而言“时间沉淀了一切”。 2021年7月24日,凌越从广州来到上海民生美术馆做“诗歌来到美术馆”个人专场分享活动,回忆了他的青葱校园生活:“1991年秋天(对,还是秋天,这是我的诗歌季节),我们的宿舍被挪到了河东的学生宿舍,那是建于新时期的毫无特色的水泥楼房,宿舍空间很逼仄,如果无所事事的室友们凑齐一桌牌局,那宿舍里的喧闹就可想而知。一天下午就是在这喧闹声中,我带着几本书和笔记本走出宿舍,打算去不远处的教学楼。经过一间简易餐厅,它的铁皮屋子被漆成了蓝色,那时候也已经变得很斑驳了,然后经过一家简陋的私人开的餐厅,我还记得它有一个朴实的名字叫快乐餐厅——刚刚拿到家里汇款的同学会来这里改善一下生活,再往前就是同样毫无特色的河东教学楼。这些建筑都是邻苏州河而建,那时苏州河还未经除污处理,河水是黑色的,一到雨天,河里沉渣泛起,整个校园里都飘荡着令人作呕的恶臭味,但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它只是散发着淡淡的腥味,还不致影响到我轻快的心情。在一楼我方便地找到一间空无一人的教室,我在临窗的位置坐下来,把笔记本打开,那是一本黑封皮的笔记本,里面已经涂满了青春的诗行,多半这些诗是我在上毫无兴趣的法律课时写下的”。 透过诗人自述的这些于平凡生活中攫取的意象,可以感受到凌越对于生活的细致观察、思考以及诗意生活的洒脱态度,读这样的诗让人感同身受。 同样类型的“小诗”中,另外一首《赠我一行诗》最后两句尤为我喜爱:“以诗句的风筝线/以星光柔弱的拐杖。”将“诗句”喻为“风筝线”,将“星光”比作“柔弱的拐杖”,这是非常精准的个人感受,这样细腻传神的比拟,读来如春风拂面。 四、戏剧性诗人与严谨译者,以《一个在夜间赶路的人》为例 访谈中凌越谈到:“每个诗人都有自己惯常的写作路径、写作策略,戏剧性面具是我多年来写作诗歌的常用手段之一,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人会认为我是当代中国注重诗歌戏剧性的诗人。” 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凌越使用戏剧性面具有效地解放了想象力,使他的诗可以更便利地触及广泛的题材,从而获得更开阔的视野,《一个在夜间赶路的人》便是有意识加入戏剧性因素,这个戏剧性因素便是诗人让主人公戴上“面具”说话。 一个在夜间赶路的人—— 他清理星空的棋局, 将头顶上方嘈杂的星星扫到角落。 他向黑暗赠送书页的闪光。 他大声宣读时间机器运转的秘密, 并为你的无声无息脱帽致敬。 是的,走得越快,字句蹦得越多, 在混乱中连成意义的锁链。 亲密的关系充满距离—— 他摸黑走路,躲避水母 透明的身体无节制的膨胀。 你是急行军的队伍中掉队的谜语。 他不想说任何温柔的话, 瑟瑟风声垒起认知的峡谷。 行动的汗水洗涤美的怠惰, 谁都无法保证祝福会变成咒语。 诗中描述的场景被宁静的氛围所笼罩,带有某种神秘感,由第三者直陈又有了戏剧旁白的效果,以旁观者的身份获得客观描述的视角,在这样的视角下,诗人得以跳出沉闷的精神囚笼,充分审视日常生活的原生态:粗粝、质朴:“他不想说任何温柔的话,/瑟瑟风声垒起认知的峡谷。/行动的汗水洗涤美的怠惰,/谁都无法保证祝福会变成咒语。”整首诗彰显了诗人敢于对荒诞、无序、冷漠的现实发出质疑的担当与勇气。凌越的诗少有绮丽、梦幻、浮夸、文绉绉的修辞,他一定写自己内心真实感受,不拔高、不伪饰,语言冷静睿智,语感沉着抒朗,全然没有玩弄修辞与堆砌词语的浮浅陋习,也没有装腔作势的伪崇高与假大空。 凌越在诗中擅于使用戏剧性的特征恐怕与他“译者”身份有关,这些年他和梁嘉莹合作翻译了美国诗人马斯特斯《匙河集》,《兰斯顿·休斯诗选》《赫列勃尼科夫诗选:迟来的旅行者》《荒野呼啸:艾米莉·勃朗特诗选》等,在翻译中“经常边翻译边被那些精彩的诗句所打动,叹服于它们奇诡的想象力,叹服于它们将经验融汇于语言的能力。”其实远不止于在翻译中接收到的这些,在凌越丰富繁芜的阅读书单里,他已然“从特拉克尔、马拉美、瓦雷里、博纳福瓦、特朗斯特罗姆的深井中,开掘汉语的幽远灵性。”(参见张晓舟《生活不在别处》一文,《新京报》2010年6月11日)。 凌越作为严谨的“译者”,他从翻译中获得的养料滋润他自如地从抒情诗人向戏剧诗人转化,诗中增加戴着“面具”的他者,把习惯性沉浸于自我中的诗人唤醒,逼着他客观打量、理智审视外部世界,如此,诗人的敏感内心才能通过与外部广阔的视野有效对接,产生出激动人心的优秀作品。这样的诗作还有《拉大提琴的姑娘》《我终日躺在弹簧外露的旧沙发上》《你真是个怪物》等。 五、“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以《铜官山》为例 诗集《飘浮的地址》中,还有一批描写故乡山山水水,表达乡情、乡愁的诗,如《铜官山》《江南的暑热蒸发弯曲的梦境》《一场迟迟未醒的梦》《外婆倚在门框上》《时间的残渣》《闷热的夏夜》《我徜徉在林荫道中》等,或许从他的成长经历既可以看出端倪也可以找到答案,17岁离开家乡安徽来到上海读大学,21岁大学毕业接着又到广州工作至今,这种少小离家的乡愁乡情潜意识一定萦绕在诗人脑中挥之不去。他乡已经变成家乡,故乡却又变成他乡。既然诗人要通过诗歌表达自己对世界、对人生、对生活的见解,就一定离不开自己的情感经验,这些情感经验里或多或少涵盖了对爱情、亲情、友情的感悟,如他在《给外婆》深情写道:“不能逆转的事实是成年——而又不能返回,/事实上,我们是被逐出了那个世界。/凭藉幻想造访朴素的房子,朴素的街区和天空,/但我们手里紧攥着一片虚无。/认领吧,这一段无主的时间;/告慰吧,我还能长久凝望落日倾泄的忧郁金流。/时光永逝,外婆亲手雕刻着我的童年,/用缝补衣物的针线。/——这是脆弱的善的拿手好戏,/我得学会观望,成年碌碌无为。”对外婆没有深厚的感情断然是写不出这样动人的诗句。诗人抒写了对童年生活略带忧伤的美好记忆:“马眼般的路灯多黯淡,几个伙伴/奔跑着,黄色书包拍打着小屁股。//那是儿时某一次回家的路,/那是必将走过一生的路。”读毕让人怅茫万分;在《江南的暑热蒸发弯曲的梦境》一诗中,他乡变故乡,故乡变他乡的心结有真切的描写:“江南的暑热蒸发弯曲的梦境,/故乡就是烈日暴晒下从实变虚的地方。//长江路上穿梭的车辆,/载走成吨重的少年心思:/在星空下乘凉,/孩子们欢快地驱赶着蚊虫。//铁路小学逼仄的院落里,/我见识过癫痫病和小痞子。//荒凉的钢铁厂,妈妈牵我的手/走过那条有驴车经过的砂石路。//——回到这里,/为何总是失语?”幽深的时光隧道令人难以一眼洞穿,厚重的情感失落让人难以承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谈到写诗讲究“有我之境”,读完凌越以《铜官山》这首诗为代表的一批乡愁诗,分明觉得诗人抒写的乡情由“有我之境”升华进入“无我之境”。以《铜官山》为例: 拒斥景观的山, 埋葬道路的山, 我始终在走近却从未抵达的山, ——甚至我从不曾留意过。 放送落日和朝阳的山, 你用手把童年推开, 你把自己安放在脚和眼睛之间, ——可以看见却不能被亵渎的山。 你挺立在故乡的界石旁, 你催生的行吟诗人将终生围绕你流浪。 哪怕他们在雪的重压下四处奔逃。 静默的山,高八度颤音中那只下沉的锚。 对故乡铜官山的场景描写,不难体会一切可感之物均在诗人笔下鲜活地展示出来,家乡的记忆在进入中年的诗人脑海里依旧无比清晰,家乡的“落日”“朝阳”“界石”“路”“山”犹在眼前,诗人打开自己的想象翅膀重回故乡。所写之物,无不有情,莫不有性,莫不以此见之。这种由“有我之境”升华进入“无我之境”的精神生机由此罄露,诗人写出感受的真挚,写出情感的真诚,大大提升了诗意的深邃和诗境的价值,成为个人情性的真实记录,由此唤醒所有被时代潮流裹挟而远离家乡的游子的情感共鸣,这样的表达无疑也承担了我们时代的某种精神诉求。 六、结束语:诗人的尊严只存在于美妙的诗句中,而不会在任何别的地方 诗集《飘浮的地址》分为三辑共计150首诗,题材广泛,视野宽阔,这本质地优良的诗集有力地传达出凌越的声音:冷静、含蓄、机智、睿智,闪耀智慧光芒,具有坚定的力量,他擅于将人物外在生活与人物内在追求揉为一体,擅长将历史与现实勾连共处,语言淬炼、技法娴熟、诗意盎然,优美的意象与流畅的韵律浑然于一体,现代气息浓郁。通篇读毕获得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这种共鸣其实就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心意相通。 千百年来,写作者的使命似乎就是孜孜不倦地把人类相同或相似的际遇、阅历、体验、感悟所形成的情感和认知精准贴切地表达出来。凌越的诗歌就本质而言,都是内心的映像。诗人、批评家、译者的三重身份使凌越拥有开阔的视野、胸襟与格局,在当代诗歌现场发出的声音不仅掷地有声,而且穿透人心。之所以从诗集《飘浮的地址》获得一种情感的共鸣和力量,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正源于此。 借用诗人在访谈中的一句话作为该文的结束语:“诗人的责任首先在于能否给本民族语言带来活力,换言之,诗人的大敌永远是陈词滥调,诗人的想象力、道德感,只有在语言创新的基础上才有实现的可能。……作为诗人,写出好诗就是最高的道德。诗人的尊严只存在于美妙的诗句中,而不会在任何别的地方。” (2022年9月8日写于上海,原文发表于2022年第2期《中国汉诗》,有删改。) 【凌越】诗人,评论家,译者。安徽铜陵人,现居广州。著有诗集《尘世之歌》《飘浮的地址》,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见证者之书》《汗淋淋走过这些词》,和梁嘉莹合作翻译美国诗人马斯特斯《匙河集》,《兰斯顿·休斯诗选》《赫列勃尼科夫诗选:迟来的旅行者》《荒野呼啸:艾米莉·勃朗特诗选》等。主编“俄耳甫斯诗译丛”。 【崖丽娟】《世纪》杂志副主编。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被评为中国诗歌学会“2021年优秀会员”并有诗歌获奖。在“南方诗歌”开设“崖丽娟诗访谈”专栏,诗歌、评论、访谈见于《文艺报》《文学报》《解放日报》《欧洲时报》《诗刊》《作家》《作品》《上海文学》《诗选刊》《诗林》《草堂》《中国文艺家》《百家评论》《安徽文学》《山东文学》《广西文学》《芒种》《鸭绿江》《滇池》《南方文学》等数十种报刊。 供稿:原作者 | 责任编辑:牧 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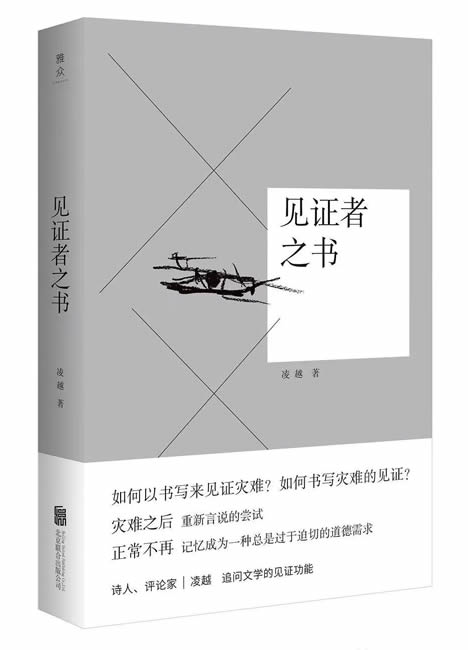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