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刀不老 文火微妙 —— 张新泉先生诗歌版图探析
好刀不老 文火微妙 ——张新泉先生诗歌版图探析 徐玉财 数十年间,很多人都大变特变了,变得面目全非,唯张新泉从来都是神清气爽,气宇轩昂,骨骼硬朗,胸怀宽广。那么多的辛酸苦辣,没见过他呼天抢地……当我们遇见“好刀”“文火”在一起,几乎毫无差别地都会想起诗人张新泉。
一、小荷才露即沉水 1941年,张新泉出生在与富顺县城一江之隔的沙湾——一个曾经富足殷实的大地主家庭,当然也是书香门第。随着社会的革故鼎新,张家被改造,偌大的院子变成了后来的沙湾小学。 受家学渊源影响,张新泉诵读了大量古诗词,为他日后诗歌的古典风韵打下了坚实基础。少年时代,张新泉进入富顺二中读书。他先后在《少年文艺》《工人日报》等刊物发表诗作。小荷才露尖尖角,特殊年代,因张新泉办了一份名为《火炬》并自任主编的油印小报,被认为是思想反动而被开除了学籍。厄运像一记重拳,将诗人年轻的头颅强行摁入水中,改变了梦想的锦绣前程。 离开学校后,张新泉去富顺糖厂打临工。遭遇国家经济困难时期,18岁的张新泉被分流到富顺运输公司邓关站,他选择了拉船当纤夫。离开纤道后,张新泉来到邓关码头当搬运工。 1964年,张新泉调进富顺县川剧团做乐手。后来,他又调回富顺糖厂,主动要求到铁匠铺打铁,以便于阅读那些四处搜罗来的“毒草”名著。这是对张新泉那些“沉水”日子最好的安慰和救赎,给予他的诗歌以崭新的题材和特别的意义,并让他在创作中抛弃了繁复的花样,用生动的简洁来铺陈,有如宋词元曲的长短句,更像火星四溅的铁花。 1979年底,宜宾地区文工团调派张新泉去团里当创作员。他陆续在各大报刊发表了不少诗作,还加入了四川省音乐家协会,并荣获第一届四川文学奖。
二、纤绳脱水而飞 1985年,《男中音和少女的吉它》出版,这是张新泉面世的第一本诗集,收录了诗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诗作63首。清新流畅的语言,超凡脱俗的构思,独具匠心的结构,颇有冲击力的阅读节奏,使得张新泉的诗歌一登场就非常亮眼。 诗人张新泉从“沉水”里挣扎过来,很快进入创作的丰水期。其书名主打诗《少女和她的吉它》,激越又委婉:“望眼中的水鸟/总在音箱里盘旋/谁知是在解缆/还是在收纤//岸地起伏的线条/逼退江面的平淡/水手的缆绳抛来/变成她怀中的七弦//一颗温润的红豆/跳在海魂衫上面/琤琤琮琮的琴音/颤栗了所有的桅杆……”全诗押以“an”韵,耐人寻味。 这首诗写于1984年11月,诗人时年43岁。其时的季节,江水应该归于平缓,而颤动的心弦依旧激烈,诗人猛地回想起自己的拉纤岁月:水鸟、音箱、线条、红豆、琴音、桅杆、海魂衫……一众物象与意象混响在一起,纤夫的缆绳忽地脱水而飞,变成了少女怀中的七弦,连桅杆也为之震颤。这是既懂音乐、又有拉纤经历的张新泉才能营造的诗意铺排,形象美与抽象美在此合二为一,让读者读出了纤夫的别致多情。曾经惊险“沉水”的苦难终于跃出水面,幻化成诗人的不绝诗行,铮铮行走于诗的领地,彰显出诗人的特立独行。 但凡经过大风大浪大起大落之人,都希望迎来生命的沉思与沉静。只是,静水流深,诗心不死,一旦泛起涟漪,很快就会让跳跃的思维脱水而飞。 1989 年,张新泉第二本诗集《野水》出版。那是纤夫题材的系列诗作,是他横空出世的成名之作,一汪“新泉”浓烈为一莽“野水”,旁敲侧润着中国诗坛。张新泉在《题照(代序)》里这样讲述:“生命的纤道上/有太多的坎坷/我才咬着一支号子/抗拒窒息和沉没//一切优美甜柔的/都不在这里/你看这额头这瞳仁上/尽是风涛、雷雨”。诗人张新泉,就是那位搏击野水的勇士,酣战于激流险滩,迎头撞击风涛雷雨,全力“抗拒着窒息和沉没”。 凡是命运的强者,无不是这样闯过来的。这让张新泉的诗歌具有了普遍的审美倾向,赢得了更多的共鸣与共情。 “张新泉通过对纤夫生涯的摹写,对水与江河的赋意,以雄浑、强悍和极具张力的诗句,透露出野性的力量、生长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这些作品摇曳生姿,具有一种阳刚的、粗砺的美。”(聂作平:《我的亲老师张新泉》) 在《滩头》一诗里,张新泉从容写道:“岸边,一位白衣少女/正在画架前挥笔忙碌//画:拽得冒烟的纤绳/画:鼓成块状的肌肤//不知我们嘀嗒的汗珠/会不会濡湿她的画布//不知她用什么线条/表现静止的拚搏,倔强的匍匐……” 船上块状的肌肤和冒烟的纤绳,岸上白衣的少女和忙碌的画布,船上岸上互为呼应,呈现出“诗中有画”。“静止的拼搏”与“倔强的匍匐”彼此渗透,画面感十足,诗意飞上画布,成全了“画中有诗”。诗人在具象与意象之间随意切换,并在急促的画面里将白衣少女置入其中,让纤夫与少女构成力与美的对应。即便在艰难险恶的岁月里,诗人也从未忘记对美的尊重(会不会濡湿她的画布),并以此获得美的安慰……野性的纤夫,娴静的少女,一起为滩头绘出一幅更大的画布,让读者深陷其中,仿佛那冒烟的纤绳立马就会燃断脱弦,直击人面。 再来品鉴这首更为劲道的《拉滩》:“在滩水的暴力下/我们还原为/手脚触地的动物//浪抓不住我们/涛声吼叫着/如野兽猛扑……是的 这就是匍匐/一种不准仰面的姿势/一种有别于伟岸的孔武//热得嘶喊的汗/一滴追一滴/在沙砾上凿洞窟//船老大在浪上咒骂/骂得无法无天/骂得好粗鲁//轮到我们骂时/我们只仰躺着喝酒/仰躺着把匍匐报复……” 人生如逆旅。这样的“匍匐”,是上坡时的奋力攀爬,是吃力时的紧紧咬牙,更是逆境中的顽强拼搏。待到越过险滩,攀上平地,便以胜利者的姿态举起酒杯,“把匍匐报复”。这样特立独行的表述,只有诗人就是局中人,才能抒写得这么透彻,让人侧目。纤夫的“匍匐”与“纤绳”,构成一组应力,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相应增加。当应力大到一定临界点,就会出现“纤绳脱水而飞”的事件。所以,我们在张新泉的纤夫组诗里,无数次读到“匍匐”一词,甚至读到“匍匐在匍匐的卵石上(《纤道,姓名》)”,颇有博尔赫斯“就像水消失在水中”的意蕴之妙。毫无疑问,“匍匐”已成为张新泉诗歌王国的意象雕塑,足以在沧浪的“野水”里变得永恒。 《喊风》《补帆》《疯妇》《野码头》《水的干渴》《纤夫之死》《船夫的履历》……那些与拉纤有关的诗,都被一个叫“张新泉”的纤夫牢牢攥着,在野水驱使下,攥成“力与美”的对峙与守望。诗人向以鲜说:“纤绳带给诗人张新泉最为深切的影响,不是痛苦的牵引,不是滚烫的汗水或泪水,而是一种锲入骨髓的力量和旋律。” 到了《遥途》一诗里,诗人娓娓陈述:“航行在无滩无激流的平水/嘴边的号子也昏昏欲睡/船在丝绒般的河面上滑行/仿佛背上的纤绳稍一用力/那轻巧的木船便会脱水而飞……” 习惯了激流险滩的纤夫,到了“丝绒般的河面上”,反而有了失重的感觉,连“号子也昏昏欲睡”。此时此刻,“纤绳稍一用力”,连木船都会“脱水而飞”。是啊,当张新泉离开河岸离开水边,面对未来不确定的“遥途”,内心的怅然及其带来的心理起伏,该如何调整与顺应飞速变化的世界呢? 纤绳脱水而飞。“从青青的竹子 到/褐黄的纤索/你说 我像不像一首歌(《残纤》)”。纤绳,是几股青色竹篾绞绕为绳索,经过特殊浸泡处理,变成褐黄的纤绳,其韧性十足,其受力无穷,其生命来自岁月的淬炼。“纤夫诗人”的标签就是这样贴上的。 纤绳脱水而飞。飞跃暗礁,飞出欲海,跃上缪斯的肌肤,张扬出一片诗歌的灵性天地。这是纤夫张新泉的凤凰涅槃,是中国诗歌之幸运。无疑,作为纤夫诗人的张新泉,那段令他铭心刻骨的赶河经历,成就了他独具个性的诗意书写。 当我们观览张新泉先生《好刀》的折页签名,呵,像迎风起舞的风骨,像极了脱水而飞的纤绳,充满倔强的个性与生命的张力,动感而粗犷,骨感而飘逸,亦如百炼钢丝化作绕指柔。那签名,更像是挥舞的铁锤,运斧成风,砸出优美,砸出崇高,砸出又一番诗意天地。
三、刀光谦逊如月色 《野水》出版当年,诗人张新泉事实上还没获得全国性影响,但其独特的诗风带来的崭新气息,慢慢被更多人瞩目,在更大范围内掀起波澜。《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等名刊都以组诗的规模,相继推出他的野水系列。 张新泉的诗歌题材独特,表达简洁,诗味别样,视觉切换迅疾,具有文本探索的意义。在那个诗派林立的年代可谓独树一帜,自然赢得了无数诗迷的拥趸。张新泉很快在中国诗坛声名鹊起,其创作也呈现井喷之势。 很快,诗集《微语·情诗73》(1990年),《95首抒情诗和7张油画》(1990年),《人生在世》(1992年),《情歌为你而唱》(1993年),《宿命与微笑》(1994年),《鸟落民间》(1995年)等相继出版,几乎是一年出版一册诗集,让人仰视。 当纤夫诗歌在中国诗坛登峰之后,张新泉没有继续沉湎于这个题材,而是把目光从河岸转向铁匠铺,转向从普通人生中捕获精微幽暗的诗意,“铁匠诗人”呼之欲出。这些作品,以《好刀》《文火》等最具代表性。 一提起“张新泉”三个字,《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的第一反应是:此人是个铁匠。在《打铁生涯》一诗中,我们读到了那些“穷欢乐”的时辰:“我在打铁铺呆了六年/常常是铁已烧得冒汗/却并不去打/有时突然闯入一群知哥知妹……逢到这种时候/打铁铺一派节日景象/砧板乱响/鸡毛飞扬……” 再读张新泉的“铁匠”诗《班后》:“炉膛里的火花熄灭了/胸膛里的火苗却灼灼飞腾/我知道诗的坯件已烧得通红透亮/此刻,正需要我将它锻打成型//掏出纸烟盒,铁砧上铺平/发烫的笔杆挥写不停——/录下锤声,录下火花/录下锻工对党的全部赤诚……我的诗虽像手茧一般粗糙/却蕴藏着亿万千卡闪光的热能”。刘半农曾写过一首诗《铁匠》:“叮当!叮当!/他锤子一下一上,/砧上的铁,/闪着血也似的光,/照见他额上淋淋的汗,/和他裸着的,宽阔的胸膛……”显然,刘半农的《铁匠》只是局外人的见闻,总觉得中间隔着点什么,可以听见叮当打铁声,却写不了当事人张新泉那样的心手相应。 打铁六年,早已身手不凡,张新泉终于为我们捧出了他精心锻造的《好刀》,成为张新泉的一张名片。 龚学敏认为,《好刀》这首诗就是张新泉本人。他在“张新泉诗歌品鉴会”上发言说:“面对生活,他总是把自己放得很低,这种低,不仅仅可以开拓诗歌写作题材,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人品和人格高起来……因为他有一种对铁中的渣滓过敏的天赋。一切不能入诗的,一切与他价值观相抵触的,在他的系统中会自然过滤……新泉老师就是一位手艺高超的铁匠,他有那种点石成金的巫术。” 《好刀》,究竟是怎样的一把刀? 好刀不要刀鞘 刀柄上也不悬 流 苏
凡是好刀,都敬重 人的体温 对悬之以壁 或接受供奉之类 不感兴趣
刎颈自戕的刀 不是好刀 好刀在主人面前 藏起刀刃 刀光谦逊如月色 好刀可以做虫蚁 渡河的小桥 爱情之夜,你吹 好刀是一支 柔肠寸寸的箫
好刀厌恶血腥味 厌恶杀戮与世仇 一生中,一把好刀 最多激动那么一两次 就那么凛然地 飞 起 来 在邪恶面前晃一晃 又平静如初……
人类对好刀的认识 还很肤浅 好刀面对我们 总是不发一言 这首诗写于 1991年,将“好”字与“刀”奇妙组合在一起,解放了“刀”字,让“刀”获得了尊严,让这把人化的“好刀”可以很顺当地流传下去。 张新泉的这把好刀,就这么晃一晃,中国诗坛便多出了几分清凉的月光。这把好刀不悬流苏,敬重人的体温。这里的“人”,是正常、正规、正气、正色之人,那些乌七八糟的请走开。 这把好刀,刀光谦逊如月色。这正是“铁匠”张新泉留给我们的直观印象,也是“诗人”张新泉鹤立诗坛的独特属性。鲁奖评委曹纪祖说:“那种‘谦逊如月色’的刀锋,含而不露,实在与‘剑拔弩张’的表面强横有天壤之别。在冷静与宽容背后,是更为强大的震慑力量。” 这把好刀,刀光谦逊如月色。这“谦逊”,是一种沉默与沉稳,是一种教养与隐逸,包含了看清某人不说破的格局,和厌恶某人不怒目的释然。这意味着诗人渐渐收敛了火气,慢慢进入“文火”的思辨禅境。 这把“谦逊”的好刀,一生“最多激动那么一两次”。我们不知道,张新泉这把“好刀”激动的那一两次,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什么地方,是面对什么情状。因为,诗人有铁匠的样貌,却是谦谦君子的内里,他早已完成个体生命的心理建设。所以,我们从没见他任性过,怨恨过,咆哮过,狂喜过。 评论家陈大华评论《好刀》:“终于有人认出了这把好刀。在刀剑林立的诗江湖,不乏沿街叫卖舞枪弄棒者,不乏占山为王自封大师者。细看,多是些虚张声势花拳绣腿的主儿。存世的好刀不多,回看历史,一个朝代就那么几把。张新泉这把好刀,或许有望留下来”。 已故巴蜀学者、著名媒体人伍松乔在《有一种文火叫张新泉》里说:“文火功夫或许是新泉作品丰厚、纯正、醇香的秘方。” 张新泉这把好刀,是诗歌炼丹炉里的“文火”淬炼出来的。“刀光谦逊如月色”,我们找到了它的初始密码。 张新泉辟出的这簇《文火》,不动声色地燃烧在中国诗歌的原野上,让“诗歌大省”四川更加名副其实:“在火族中 能燃得如此/漫不经心 风度十足者/必经多年修炼/看那入定似的神态/不摇不曳 声息俱无/任你周遭雨去风来/冷暖嬗变/依旧一副恬淡容颜……/单是这点功夫/就令那些/啸叫山野的浪火/打家劫舍的猛火/刮目相看”。 评论家蒋涌在《一把不显而贵的“好刀”》里写道:“这一团‘美丽而刚强的文火’一自闪亮《诗刊》,便以扑不灭的光焰吸引了一束束读者射来的欣悦视线。”这簇“文火”,也是张新泉老家点拨富顺豆花的最佳火候。 一汪新泉,一莽野水,一把好刀,一簇文火,催熟了“纤夫”和“铁匠”两个水火兼容的硬汉形象。这是中国诗歌的四川标签,这是诗人张新泉奇崛的诗性存在。张新泉,这把野水淬炼的好刀,这把文火锻铸的好刀,就这样凛凛矗立于中国诗坛,成为诗人极高辨识度和极具个性化的独特意象。
四、《鸟落民间》获鲁奖 随着张新泉诗歌的影响力逐渐扩大,首先在川内获得了更多层面的认可和嘉奖。鉴于张新泉的诗歌魅力,和他为推动四川新诗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省内文坛的最高奖——四川省文学奖先后三次颁给了他。 1998年2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首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这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57岁的张新泉凭借诗集《鸟落民间》摘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并从这一年起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这是对张新泉取得的诗歌成就的最大肯定,是对他前二十年文学生涯的高度认可。 在《烤薯店》中,张新泉写道:“我想我注定是民间的土著/离垄沟最近/离宴席很远”。在《民间事物》里,诗人自警地说:“向民间的事物俯首/亲近并且珍惜它们/我的诗啊,你要终生/与之为伍。”加上他一贯的“在低处歌唱”,表明了诗人的精神维度和生命底色。这样的“民间”,便蕴藉了“好刀”那种谦逊的本色。在乱花迷眼的文学名利场,保持佛系静穆的定力,足以平息尔虞我诈的算计,平息刀光剑影的纷争。只需读读那些以“好”字入题的系列诗作,便令人敬意有加:《好水》《好酒》《好人》《好狗》……此时,诗人张新泉已然远离“野水”,远离“铁火”,回归于市井红尘的烟火清欢。 在《小老乡》一诗里,张新泉写道:“活着容易/活得本色不容易/本色就是生命的原味/是故土的睡莲/笑在自己的静水上”。谁人不喜欢这民间气息浓烈的故土微笑?清泉煮茶,围炉夜话,远离庙堂,在自己的天地里做个自在的王。有人评价李白说,“真正的人格魅力正在于对权贵体系的疏离,在于对本真自我的看重。”毫无疑问,张新泉就是具备这种人格魅力的本真诗人,足让更多具象与意象和谐相处在一起。张新泉的笔触指向平凡人间,几乎到了无一物不可入诗、无一事不可感悟的境地。艺术意象凝聚人生境界,无穷的书写对象,让张新泉的“民间”一望无际。 张新泉的诗歌,有下里巴人的亲切,更兼有阳春白雪的艺术美,比普通诗作多了几分音乐气韵和古典气质,如随处可见的复沓吟咏:“被七月 烤过/被数九 冻过/被汗 咬过/被水 泡过/被逼成刀锋/把礁石砍过//是把尺 量尽纤道/是根弦 弹遍长河/哭过 醉过……(《残纤》)” 在《乡亲》一诗里,诗人张新泉不无忧患地写下:“听说村头的地都荒了/野草高过门前的篱笆/挤在出租屋里的乡亲/ 活在霓虹灯影中的乡亲/听说谷垛塌了,磨坊哑了/就对着手中的钞票发愣/就学会了失眠、说梦话”。这首诗写于1994年,快三十年了,今天的村头撂荒地多了去了,也没人再码放谷垛了。我们的“民间”,我们的故土,完全被改写。诗人啊,一晃三十年,您的“民间”又在何处安放? 这不,我们在龙泉驿桃花诗歌墙上看见了那个“民间”,看见了那个妇孺皆知的“桃花才骨朵,人心已乱开”的金句。实际上,在富顺民间,有一句喜欢开涮人的俗语:“人家姑娘才起花骨朵,你们就在乱打主意啰”。其情其景,经过张新泉神奇的诗意点化,恰到好处地呈现出来,一下就疏朗了那些堆积如山的桃花诗,让去往春天的道路变得豁然,让人面遇见桃花便直插入心肺,遂成为龙泉驿桃花诗的“诗眼”。这是文字的鬼魅,这是诗歌的使命,这是生活的有心,更是诗人的匠心。 鸟飞民间,鸟落民间。张新泉潜在民间的世界里,看花开花落,任云卷云舒,依然明月故乡,依然诗意昂扬,不时带给我们惊喜。 2016年7月,张新泉凭借诗歌《与老为邻》,荣获《中国作家》第五届郭沫若诗歌奖。老树着花无丑枝。这一年,张新泉75岁。 2017年2月,“2016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颁奖会在北京发布,诗人张新泉与作家贾平凹等一起,摘得“优秀作家贡献奖”。 2019年3月,张新泉新诗集《事到如今》发布,使他成为首位入选“中国好诗”的四川籍诗人。所有的风光都会过去,而热爱诗歌却不离不弃。张新泉说:“到现在我仍然爱诗,非常热爱,好诗看一遍还不过瘾,我要抄到一个小本上,总有几本书对你影响至深,如同总有几个人对你至关重要。”欣赏别人,正是张新泉一直保持着旺盛创作力的原因之一。
五、众说纷纭张新泉 2017年国庆节,富顺豆花文化旅游节期间,“张新泉诗歌品鉴暨‘富顺诗歌现象’研讨会”在张新泉的故乡富顺县举办,被文坛称作“诗人大返乡”。那是诗人来路与归途的一次高度重合,那注定是富顺“诗颜值”最高的一次。瞧瞧与会阵容:吉狄马加、商震、李加建、曹纪祖、龚学敏、李自国、李华、王孝谦、牛放、凸凹、聂作平……还有自贡及富顺本土诗人作家一大群。大家只为一个人而来:张新泉。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所有莅临的诗人,那一天都跟着张新泉一道返乡,一道诗意地栖居在富顺的大地上。吃豆花,走天下。到了该返回的时候了,去看看豆花如何赋予诗人一腔浪漫。 研讨会上,吉狄马加脱稿娓娓道来,他说:“张新泉是一位根植民间生活、诗歌始终贴近现实和人民的实力派诗人,他的作品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注重对细节和微观世界的生动呈现。” 商震说:“无论在《人民文学》期间还是在《诗刊》期间,我都亲手编辑过张新泉老师的大量诗作,都为其独具个性的诗歌特色和独具视角的诗性魅力所深深折服……他从底层生活提炼出来的诗,很接地气,干净又纯粹。他诗如其人,通透豁达。” 李华说:“张新泉以他不懈怠的诗歌创作和诗歌高度,最先投影了他家乡的富顺县,因此才有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诗歌原生带。”张新泉的出现,带动了家乡的诗书风气,形成了富顺文学链条,丰沛了富顺文脉。作为老乡老友的李华当然清楚,张新泉就是“富顺诗歌现象”的引爆者。 曾与张新泉同在富顺文工团工作的剧作家廖时香评价说:“他的诗也越来越穿得少,剥去一层层繁琐的浮词,句子放在铁砧上锻打、淬火,最后呈现出坚韧、骨感、温润、蕴藉。读者无不为他如此干脆而又回味悠长的造句所倾倒。” 蒋蓝说:“他的诗没有高起高打,没有大词宏句,没有阿世谄媚的堆笑,也没有惊世骇俗的厚黑技术,他的诗就像一插到底的蒿竿,穿过了欲海喧嚣的名与利,在天地间树立起了一个苍劲奇特的独立意象。” 凸凹说:“张新泉笔下的万物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各有各的脾气,各有各的好恶……善与美,是万物和平共处的钥匙与秩序机关。读他的作品,会愉悦,想着活下去,会增添几注活下去的劲力,这个是底线。这个也是张新泉作品的魅力、价值与意义所在。” 印子君说:“作为纤夫诗人,张新泉无愧于‘沱江之子’的称号”。作为民间诗人,张新泉让富顺这块诗歌高地更接地气,更有生趣。 沱江,是张新泉与故乡紧紧相连的血衣脐带,有了这一江诗意,所有的青春就可以一直蓬勃下去。豆花余情,铭记富顺。当矿化卤水遇上滚滚豆浆,当白玉豆花遇上殷红蘸水,便生成了弥漫富顺的绚烂想象。而关于“张新泉”,远不止于诗歌,那是几个时代的浓缩,是关于人生的一部大书,是关于生命的一次哲思,更是关乎心灵的一场旅行。 ……
六、山高水长张新泉 云雾苍苍,山高水长。张新泉之于富顺之于四川,可谓“诗神”一样的存在。 首先是张新泉先生的正直正气。作为“民间的土著”,张新泉不吸烟不酗酒,减少了那些不怀好意的阿谀靠近,和躬身应付世俗的虚与委蛇,更守住了诗人的纯正与纯真。什么人写什么诗,其人品人格早已熔铸于那些分行的一字一句里。再读张新泉《骨子里的东西》:“我们景仰的/美德和品性/也住在206 块骨头里/与之相逢/是我们的福分/它们阳光一般/使生命神清气爽/气宇轩昂”。他的光明磊落,与一些人的自私刻薄可谓对比鲜明,高下立判。 其次是张新泉先生的重情重义。早在知青年代的富顺糖厂,以“铁匠”张新泉为中心,一群热爱文学热爱诗歌的知青朋友,乐得从四处赶过来“朝圣”,在富顺糖厂月朗星稀的院坝里收获“致青春”的旷世友谊。张新泉在家乡还收获了“富顺文化守望者”荣誉,他很珍惜这不起眼的称号,来自家乡的厚爱有时超过国王的加冕。重情重义,更体现在张新泉对诗歌新人的无私扶持上。他一如既往地提携新人、鼓励友人。他的古道热肠,让人如沐春风。整个川南诗群的诗人,或多或少都带着张新泉的印记。感恩遇见,从做人到为文,那种学生对恩师由衷的心仪和敬重,是别处极少见到的。张新泉唤醒了富顺人慷慨大气、重情重义的传统禀赋,强大了“富顺诗歌现象”的气场。 再次,也是核心的原因,那就是张新泉及其诗歌的现象级标杆式存在。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给予张新泉的颁奖词为据:“作为一位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老诗人,张新泉一直葆有对诗歌纯真的热爱,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张新泉的作品,语言质朴、简单、干净而鲜活,情思隽永,具有很强的时代感,不故作高深,他笔下的普通事物和日常生活,都彰显着浓郁诗意与不凡的创造力;他关注自然、生命和社会众生心灵,对世界怀有深情,对生命理解透彻,更难得的是他一贯在诗中传达出的温暖悲悯的情怀和坚忍达观的态度,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在一位诗人生命中的生动体现。”张新泉营造的非凡意象世界,和敢于突破形式创造新奇的遣词造句,已有开宗立派之功,他却不自立自封。 第四,是张新泉先生超级丰富的人生体验,这是独一份儿的。将人生阅历和生命感悟写入诗中,从表象里攫取抽象的诗情,从物象里碾磨具象的诗意,非经历不足以成句。张新泉从来都不疾不徐,对“汲汲乎功名利禄之徒”不屑一顾。这与当下网络汹汹、流量争宠的博眼球文化截然相反。张新泉们独具一格的诗意存在,或将是人类打败智能写手最后的救命稻草。 活着的意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活着,以生命的长短而论;一种是诗意地活着,以生命的精彩而论。可以确认的是,张新泉活出了两种意义。抑或,他根本早就不在乎这些了,就像好刀“对接受供奉之类不感兴趣”。这样的诗人,借用富顺民间口语的说法,我们希望张新泉先生“百岁当零头”。 2022年,《好刀,野水及其他——张新泉自选集》出版。这是张新泉最近结集出版的诗集。诗人继续用诗歌完善着个体生命,诗意随时可以逢境而生。诗意延年,诗歌养人。即便已年过八旬,诗人依旧身体健旺,思维敏捷,机趣不减,佳作不断,骨子里仍透着阳刚之气。 “底气丰沛的人/常在谷中散步/顺手摸摸树上的文字/花就开了《关于底气》”。很多年过去了,那底气依然饱和。
七、权作结尾 “以一生的时间,向宿命微笑”,多处看到张新泉先生的签名赠言。他的豁达通透,掩在那首叫《火葬场的烟囱》里,诗人把那烟囱说成是无孔之箫,箫韵悠悠,一下让可怕和悲伤随之顿消。往生之路,不过是此在生命的另起一程。 “已是资深老年/却迟迟未能痴呆/看乌鸦,照样黑/观侏儒,依旧矮(《自画像》)”。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这样的人间清醒,这样的审美趣味,满含张新泉八十年人生的硬度,更像搁久的普洱茶,越陈越香。 八十出头了,满头白发了,不必仙风道骨,好刀何须饰流苏,这得拜“民间”所赐。《一只鸟在回忆飞翔》《我已经活得又老又旧》《我看见迎面走来的暮年》……这些诗里的况味,自成一格。 任岁月老去,“野水”不腐,“文火”不熄,“民间”微妙,“好刀”不老。那些诗歌正年轻! “百岁当零头”,依然是我们对张新泉先生一如既往的美好祝福。
徐玉财,生于1969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富顺县文化馆文学专干,《富顺文艺》执行主编,先后任富顺县文化馆副馆长、富顺县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富顺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先后出版个人散文集《岁月倾城》《岁月铮铮》《岁月在线》,主笔编撰地方特色文化书籍《富顺方言》《富顺非遗》《富顺民间文艺专辑》等。
荐稿:崖丽娟 | 编辑:牧 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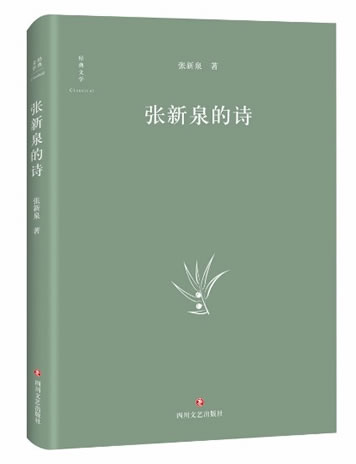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