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陆辉艳诗集《途中转折》: 时光在身后点燃,终成熠熠的星河 ...
【陆辉艳】广西灌阳人。出版诗集《途中转折》《湾木腊密码》《高处和低处》《心中的灰熊》等。作品发表于《诗刊》《青年文学》《扬子江诗刊》《上海文学》《天涯》《星星》《十月》等刊物。获2017“华文青年诗人奖”、2015青年文学•首届中国青年诗人奖、第八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参加诗刊社第32届青春诗会。 时光在身后点燃,终成熠熠的星河 ——读陆辉艳诗集《途中转折》 崖丽娟 刚过不惑之年的诗人陆辉艳是“文学桂军”中的佼佼者之一。诗集《途中转折》是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其中一本,陆辉艳以日常性写作视角不断试探着用诗歌突破常态化生活的限度,她通过使用日常词语与超凡想象力的对比营造出极富张力的诗意场景,从而为我们提供一种神奇的、动态的、陌生化的超验世界。她所写的题材或许我们早已习以为常,阅读后却总能使人怦然心动。 读陆辉艳《转折中途》诗集之前,我已经读过她《心中的灰熊》和《湾木腊密码》两本诗集,并在《诗刊》《诗探索》《广西文学》等杂志读过她的诗作,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里确认又多了一位自己喜欢的真正的汉语诗人。读陆辉艳的诗,首先感受到的不是她咄咄逼人的才气,而是从字里行间弥漫出来的气定神闲、淡然处之的生活智慧。陆辉艳的身上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沉静笃定、充满灵性、对个人经验和生命感知的敏锐、坦诚中自带锋芒和柔软的交织互映。她往返行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关注一草一木,以亲历、亲见、亲闻来关照现实,俯身低语,用动人的细节和现场感呈现生命的体悟,内敛而深情,即便对生活中的不如意甚至痛苦也有超拔的意志力和超强的自愈力;换言之,那怕是生活中的二元对立或悖论,她都能用文字进行消解。比如在《到了风雨桥》一诗中,她把自己生活中感受到的刺痛做了这样奇特的表达: “就在这里打个盹。静静地/疲乏跑过了桥。/身体还在旋转木马上/我知道我的身体,已经停不下来/像被生活这根鞭子/抽打的陀螺。转,不停地转/直到撞上一块石头。一截树桩。/它的力量使我停下来,我才能/心安理得地躺下。而在风雨桥,/这让我开始,安静下来的地方。/风吹着,风再大,也不忍心/将我这只陀螺,吹得/再次旋转起来”。正是“生活这根鞭子的抽打”,使诗人勇敢、坚韧、深刻起来。“只有足够深入地凝视存在,你才能最终觉醒于万物之中。”把诗人简·赫斯菲尔德说的这句话对照陆辉艳写作十分贴切。 诗集《途中转折》饱含悲悯与大爱,不仅有对家乡的赤诚之爱,还充满对生活于这片土地亲人的悲悯,“我一个人坐火车/从别人的城市回来/陌生站台的中转/路途的破折号//途中的N次转折/时间犹如古老的关隘,/腾出位置,允许我/回到出生的地方//在密林里,我见到了亲人/他们告诉我,在一次闪电中/一棵古老的树木断裂,在两截尚未/脱离的横断面/呈现出一副张开的枯黄牙齿/那时,我听见自己的骨骼/发出脆弱的声音”。接纳万物似乎是诗人对自己生命底色的反复确认,并以细腻的情感融入其中:“并非黑暗中的一个婴儿的哭声/尽管他们具有/相似的质地和音色/尽管它们传递的/同是时间的信息。” 陆辉艳的诗歌往往建立于自身经验之上,由此及彼探索自身及他者的内心世界,揭示外界与内在的矛盾,沉着冷峻,真实客观。在个体经验与语言之间彼此成就,反映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难怪诗人会用这首同名诗《途中转折》作为诗集名。 作为一个对故土无比眷恋的人,家乡亲情被她反复忘情地抒写,在《热爱》这首诗中,陆辉艳把记忆的笔伸向了“湾木腊”(她的家乡)这一片故土,因为热爱,“黑色的鸭子浮在水面上”像“一群黑天鹅”,又因为家园的纯粹,她“也爱过湾木腊河面上一群鸭子的喧嚣 ”。她让家乡的山水带上时光的厚度和历史的沧桑,折射时代的印记折痕,《回到小学校园》《木匠》《青麻地》《最好的风景》《环》《白纸》《奶奶》《39岁那年的母亲》《父亲深夜来到我家》等诗始终根植于故乡亲人,文本通过大量微小的细节(如时间细节、行为细节、语言细节等)描写,使山川地理、历史文化、风情俗物呈现诸般风姿:“哦,天空低垂/它占领杂草丛生的土地,犹如躯体/长年累月,为我的灵魂所租用/秋天的鸟雀跑到山顶的背面/不久将传来消息:它们啄去巢穴 ”(《状况》),从风景中汲取即时性的经验,天空、杂草、秋天的鸟雀、山顶的背面、巢穴……构建出熟悉的生活场景,在世俗化的时间流动中,这些生动的细节汇集成为诗人观察现实、发现自我的一个焦点,勾勒出中国乡村的人伦现实。与此同时,她对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逐步趋同或异化同样有着深切的体会,这与她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她出生于广西灌阳乡村,后来到广西省府南宁市工作和定居。如果说,自然风光是陆辉艳的诗歌描写的一个主体,那么,对社会的关注、对生活现象的观察,则是她着力描写的另外一个主体,诗歌的意义也从现实的裂隙中满溢而出。陆辉艳的诗里有很多表现公交车、码头、街边等城市公共空间的场景,通过这些流动的生活场景反映城乡题材转换过程中的阵痛,书写城市现代性所附带的压抑、焦虑、恍惚、迷失,诗人选择这个场域作为突破口,似乎想从这里打开进入城市的通道。如《手铐》:“这匆忙、拥挤的生活/不得不爱,不得不接受/举起双手,各拽一个吊环/哦,耶稣受难的姿势/座位上,一个坐在妈妈怀里的孩子/仰起头,指着那些晃荡的吊环/突然大声说:/看,好多手铐!”准确,凝练,不动声色对现实世界进行独特的思考和探索,诗人在车上观看城市人及其变化,反思生活,对城市化导致异化产生精神痛苦的残酷现实无情讽刺和批判。公交车上的另外一个场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以书写死亡的方式,转换成生的渴望和信念:“他挪开那上面的物件:/一个骨灰坛,盖着黑色绸布/‘坐这儿,这儿’/他的声音压低,充满悲伤/右手按在胸前”(《缺席》)。码头是城市中各种身份人群流动的重要场所,南宁“码头”这个意象主要出现在《在南宁港空寂的码头》《上尧码头》《他走进集装箱》等诗中,这些诗从“码头”出发,探讨码头、人与城市的关系:“很快,这里将弃置不用……每天来此等候买鱼的人/去了新的集市。一个搬运工,来自隆安或蒲庙/脸上有沙砾的印迹。他忙着整理行李/脸盆,衣服,吃饭用的锅碗,……一个口盅,一把牙刷……那条红色裤衩……我们来到此地/既非买鱼的人,亦非搬运工/我们远远地,站着拍照/试图定格这空寂的码头/儿子专心地挖掘沙子,用他的玩具铲”(《在南宁港空寂的码头》)。这首诗中旧码头与搬运工之间、搬运工与“我们”之间,形成了极端差异的对比,将其置于城市化不断拓进的现实语境里别具深意,诗人用含蓄代替了悲悯,揭示的是生活于现代工业城市人们的心灵处境和从乡村进入城市生活失落的现实处境。《大苹果》这首诗是陆辉艳书写街边的“流浪汉”形象:“他每天在思圣路上,来来回回地/压低帽檐打电话/有时他蹲在马路边/举着一个破手机喊:喂喂喂/有时他摘下帽子,挠着一头乱发/似乎在谈一桩生意,而且/即将成功/那天早晨我故意放慢车速/看他煞有介事地拨通电话/口气温柔得像个好父亲/“等着我,给你们买大苹果!”/这个身披破布条的流浪汉/手中举着一个脏污的/手机模型”。《大苹果》尽管生活的艰辛扑面而来,诗人却能破茧成蝶,用最质朴的语言通过对底层生活描摩显示出对一位流浪汉内在的深情。在陆辉艳这里,诗歌写作与其高尚的精神追求有关,她以潜藏在心灵深处的真诚情意,将现实的另一面形象化,并借助生命和生活体验、心智和灵感,营造出别具一格的诗歌美学,形成独特的生命历程和艺术世界,最终找到一条通向诗与远方的路径。作家阿米亥有一段话很适合借用过来形容陆辉艳:“他将生命的碎片打碎成小时,小时打碎成分秒,分秒打碎成更细的碎片。这些,所有这些,都成为头顶上的星辰,难以计数。他一路走过大地与河流,走过田野与城市,感受每一缕阳光的温度,体会每一滴雨水的甘甜,时光在他身后点燃,寸寸成灰。漫长的岁月里,与光,与影,如诗,如歌,终成熠熠的星河。” 文字来自诗人真实的经历,它释放出诗人的理想主义情结,也升华文本的精神品质。优秀诗人都不乏处理语言的能力,陆辉艳对语言不断锤炼和锻造,语言与技术结合在一起,使语言后面蕴藏极其富足的思维内涵,形成内部交流的语义循环场,情感流向丰富且多元,从而产生审美价值。在《梭罗乐意邀我去湖边耗散时光》这首诗中,她写到:“从南宁到马萨诸塞州,到/康科德镇,到瓦尔登湖。只需四秒钟/给我四秒钟的行程,我便是/天与地的素心人”。她在对自然的神往中对自我进行精神流放,叙述语言看似朴素单纯,其实内容涵义相当丰茂复杂。陆辉艳在《按内心生活,按理想写作———当代广西本土诗人访谈录(之五)》一文里,谈到《回到小学校园》的创作时候说到:“结尾有几句是这样的:教过我的老师,一个离开了人世 /两个调到了镇上,剩下一个,头发花白 /戴着老花镜,但他还是一眼 /就认出了我。去年的情人节,因为奶奶过世,我回了一趟老家,办完奶奶的后事,我去了二十多年前就读的小学。面对小学校园的物事人非,我心中的潮水汹涌澎湃。我知道,无论我如何去抒情,去感慨,都不能准确地传达我当时的心情。我只能选择白描和自言自语。我越来越喜欢这样的言说方式:冷静的,客观的,朴素的,不动声色的,我觉得这样才足以准确地表达我的情感和对世界的态度。”这完全可以视作她的诗观。如果说小说的开头是十分重要的,诗歌的结尾就很能辨出好诗人的真伪,陆辉艳很注重结尾的处理,很多诗结尾已成绝技妙技。我特别喜欢《简单生活》这首诗的结尾几句:“我记得那天下午我是怎样/穿过草地,轻快地离开江岸/为自我地一次纠正:那被过度解读地世事/那曾短暂亲近天空,最后落入筐里的鱼/”。还有《薄暮》最后两句:“那从水草间荡漾的秘密/曾短暂地减轻过我们自身地重力和恐惧”。以及《悬崖》的结尾:“他在喉咙里安上一杆狙击枪/瞄准他的命运/被悬崖反弹回来的尖锐/又再次击中了他”。不一而足,这样简单质朴却意蕴无穷的文字足以印证她的诗观。 陆辉艳的诗画面感强,视觉形象突出,在很多诗人用繁复的修饰搭建空中楼阁时,陆辉艳难能可贵地转向内心深处,凝神深思,唤醒潜意识的经验,在意识的幻灯片里反复播放生活的感人细节,她的诗有着丰沛的想象力和现代精神性。《只差一步》呈现的画面不仅有静态的意象,还有动态的意象,二者构建出强大的语言张力和内在意蕴:“那是一道闪电的开始,阳光的移动/刚好制造了一片/槐树的阴影。跳探戈的女人/双脚钉在大地上。她表情专注/仿佛另一个人紧贴她的脸/追逐、躲藏、踢腿、腾跃、270度旋转/——她搂着一个人不存在的舞伴”。槐树跳舞的前提是自己扎根于地下,而雷电下舞步的曼妙与扎根地下不可能舞蹈之间构成只可意会的某种张力,让你不由得沉浸在她用文字精心营造的丰富诗意联想之中。诗的艺术就是陌生化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对“陌生化”的一段话非常著名“艺术的存在,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感觉如同你所见到的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 在《心中的灰熊》这首诗中,她把现实的虚妄隐喻为心中的灰熊,在无谓与对抗中她便是那个在旷野的风中狂奔的战士,通过正视灰熊并对其怒吼予以回击或追踪。诗人以我观物,创造出陌生化精灵,这种陌生化的表达格外打动人心。 人到中年,也是人生的转折点。中年在人生阶段是一段相对漫长的时光,因为有了一定的人生经验积淀,通过回顾和总结,既可以从世界和生活的立场反观自己,也可以更为从容地从自己的立场关照、理解世界和生活,由此达成与世界和生活的和解。时光在身后点燃,终成熠熠的星河。祝愿陆辉艳从《途中转折》再出发,迈向更为恒远宽阔灿烂的诗意人生境界。
(发表于2024年第9期《广西文学》) 附:陆辉艳的诗 木匠
他占有一堆好木料。先是给生活 打制了一扇光鲜的门。那时他很年轻 他走进去,锯榫头,打墨线 哐当哐当,又制了一张床 他睡在上面,第一年迎来了他的女人 第二年他的孩子到来。第三年 他打制了吃饭的桌子,椅子,梳妆用的镜台 他把它们送给别人。之后 他用几十年的时间 造了一艘船。“我要走出去,这木制的 生活……”他热泪盈眶,准备出一趟远门 然而他的双腿已经僵硬 他抖索着,走到月光下。这次他为自己 制了一幅棺材 一年后,他睡在里面 相对他一生制造的无数木具 这是惟一的,专为自己打制 并派上用场的 奶奶
她是被风吹老的 牙齿一颗一颗,掉在秋天的泥地 却不发芽。她猫着腰睡觉的样子 多么像是一张蓄势待发 但丢失了箭的弓 她无力起身,说话语无伦次。“你是微微。 聋子做的豆腐花好吃。你是那个 30岁死了男人的寡婆子吗?” 脑子仿佛麻绳缠绕,如此 混乱,无法认出她的亲人 深冬的窗户敞开着 风呼呼地灌进来。“你看,死了的人在哭, 来找我了。”她端着海碗吃面 张着空洞的嘴咀嚼,鼻子眉毛上 沾满浓稠的面汤。饥饿似乎无足轻重 吃和睡成为,必须的形式 她计较生死,喜欢彻夜开着灯 “我怕黑,怕那边的人,提前来接我……” 矜持是很久远年代的事情 我的父亲,正为她烘烤着尿湿的棉被 “谁在我床上泼水?我生好火, 你们这些瞎眼人,又弄熄了它……” 她企图还原破碎的记忆,想要借助生命里 最后一点力量,踩在她曾踩过的土地上 她用力地甩了甩脑袋,这使我相信 她又恢复了神采奕奕 当我搀着她,她转过身来看我 “你是那个种桂花树的人,记着 给我留着花粉好酿蜜。”
父亲深夜来到我家
父亲深夜来到我家,他从中华路带来的 一阵冷风,惊动了客厅里的植物。 “老家在下雪。最后一趟火车晚点, 整整两小时……路上连公车的鬼影 都看不见……” 他搓着一双大手,上面的老茧一只只豁开口 它们要说些什么?
我要煮一碗热汤面,他阻止了我 “算了,我不饿……”但他管不住自己 肚子里的空气挤来挤去的声音, 它们揭穿了他。他一生都这样,不想给 任何人哪怕儿女添一丁点麻烦
他站在厨房门口,跟我说土地上的事。 “香蕉卖了,价格贱得像路边的 鬼毛针……”我从墙壁上的影子,看见 他瞳孔里长出荒草,瞬间又倒伏 他坐在餐桌旁,局促地,细数自己一生的 命运,像这片不走运的土地 父亲,但我怎么能怪你 我也同样被生活狠扇耳光 被它那只巨大的手,往嘴里灌满黑色泥浆 我们该做些什么?假装什么也没发生 置之不理:土地上的亏损、债务,苦难 梦想熄灭。直到接受这一切,直到—— 丢弃那假装的面具、踩碎 重新穿上鞋子
缺席 在西大,我乘上 回家的青皮公车。 一个男人,让出旁边的位置 他挪开那上面的物件: 一个骨灰坛,盖着黑色绸布 “坐这儿,这儿” 他的声音压低,充满悲伤 右手按在胸前 我迟疑着,坐了下去 占据一个缺席者的位置 如果我起身,走开 虚无的时间会回到那儿 而我一直坐着 跟着这辆青色怪物 过了桥,直到终点站 当我下车,并向后张望: 一排空空的椅子 缺席者再次消失 有一次 林地有蜿蜒的曲线,在秋天的庇护下 显得柔和。他惊讶于这一切: 比平常更为接近的星空 月亮硕大地,悬于头顶; 多么凉的风掀动着他 远离人群,所有的渴望消失; 月光像两只白鸽子 落在他的肩上。 面对山林,他想大声呼唤—— 除了这一切,再也没有别的 能使他心动。然而 他站在巅峰,喊得喉咙快要破裂了 但是群山仍静止 搬离 水养的绿萝也被倒掉水 装进一个塑料袋里,连同那个背电脑的 工人一起离开。你看着这间腾空的办公室 不知该说点儿什么。下午的阳光 从后窗爬进来。满是灰尘的地面 被照亮。你竟然与这些尘土 相安无事地共存多年而尚无察觉 在秩序的上面。它们被太多东西遮蔽,直到有一天 无辜地显露在阳光下。你将抛弃它们 到一个新的地方,继续耗费你的光阴,激情, 血质的孤独。你需要这样。你的可爱的同事 在对面新装修的大楼走廊上 笑着向你招手。你关上窗,但没能 关住阳光。帘子已被拆走 像每一次的搬迁,你抱着你的物件 最后看一眼那个有你气息的地方 走出去,反锁好这道门 钥匙交给另外的人,或丢掉 岛上
几只猴子嬉戏着 从树洞里觅食 风吹过南湾岛和人群 被它饲养的下午过于磅礴
渔船停靠在浅滩,有人正拿着铲刀 敲打船身的锈迹 不远处,一个女人蹲在礁石上 细心地挖着牡蛎,手中的工具—— 一把缩小了的镐头在挖着现实 牡蛎壳与岩壁融为一体 看起来,就像从石头里 不断取出鲜美的肉
大海一遍遍将它的泡沫传递过来 我弯腰,取出这饱含盐分的 天空的回音 悲伤的动物
我曾在空旷田野 见过一只悲伤的动物 谷穗和落日静静的 就在它身旁,但它看不见
我曾在一个女人脸上 见过一只悲伤的动物 排着长队的人群中 被口罩遮住的脸 只露出漆黑的双眼
在井水的倒影中 我曾见过这悲伤的动物 那是我薄弱的意志,偶然被照亮
在偏僻小路的一棵杨树干上 一扇书柜的玻璃门里 在一个人的灵魂那儿,我见过它
这些动物,不同地方的 悲伤,在互相辨认 有时它们就快要 认出彼此了
它们在黑夜里 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很快,这里将弃置不用 玉米、豆粕和鲜鱼,装运它们的船只将绕路 抵达另一个码头。每天来此等候买鱼的人 去了新的集市。一个搬运工,来自隆安或蒲庙 脸上有沙砾的印迹。他忙着整理行李 脸盆,衣服,吃饭用的锅碗,统统塞进麻袋里 被褥已用麻绳捆好,放在门前的空地上 他最后一次走进屋子,出来时手里多了 一个口盅,一把牙刷 他把它们也塞进麻袋里 之后站着抽了一支烟,抓抓脑袋,想起了什么 朝晾衣绳上,取下那条红色裤衩—— 刚才它还在风中,哗啦啦的,旗帜一样飘扬
我们来到此地 既非买鱼的人,亦非搬运工 我们远远地,站着拍照 试图定格这空寂的码头 儿子专心地挖掘沙子,用他的玩具铲 那个挑行李的男人从他身边经过 大声咳嗽着,再没有回头看一眼 这空寂的,最后的码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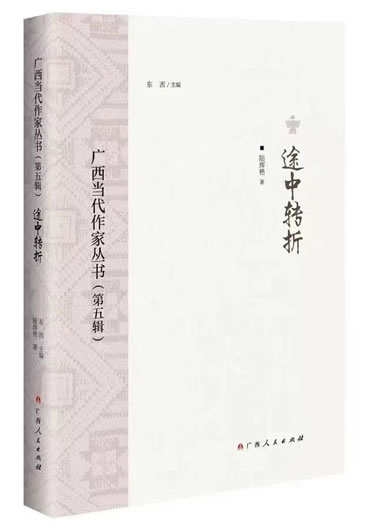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