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以反思的眼光打量来时路——序吴海歌诗集《内视镜》 ...
文/蒋登科 吴海歌不属于特别有天赋的诗人,他在1985年才开始创作,当时已经年过三十。在这样的年龄,很多诗人已经创作了大量的作品,甚至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代表作。海歌兄应该属于大器晚成的诗人,但他一直坚持着,从来没有放弃。《内视镜》收录的是诗人在2014-2023年创作的部分作品。十年时间,他选择了近三百首诗,数量不少,但和那些动辄一年写诗数百首的写作者相比,似乎也不算多。我注意到,每个年份收录的作品并不均衡,有几年只有一首,而有几年超过了一百首,这个落差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趣的信息。 一个诗人的创作在数量上可能存在多寡不同的时段,这或许与诗人在不同时期的处境、心态等有关,有时会激情飞扬,落笔成篇,有时又会暂时停笔。 智性书写是吴海歌近十年来诗歌创作的主要思维和表达方式。智性其实是带有一定理性思辨的,与诗歌的感悟性存在较大距离,但在这个年龄,经历、积累、思考已经到达了一定的深度与广度,形成了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以诗的方式把这些观念表达出来,而不是逻辑式地推演出来,可以为诗歌提供厚实的底蕴。比如《挖掘机》,诗人通过“挖掘”的动作,想象一切被埋藏的事物、精神、思想露出自身所带给作者的感受:“将僵死,化为活物/将躺下,掘成站立/将埋没,掘成坦露于天地的黄金”,在诗人那里,挖掘其实是从隐藏走向敞亮,从埋葬走向解放的过程。这种理念远远超出了“挖掘”本身,融进了诗人对历史、现实、人生、真理等的思考与期盼。从艺术上讲,诗人在表达自己情感的时候,尽可能超越内涵相似的感性,而是融入理性思考。对于年龄相对大一些的诗人来说,这种方式可以把自己的人生思考加入作品中,可以避免因为感觉力的变化而出现的呆板化、同质化、重复性等不足。 与一般的感受型书写不同,智性书写追求底蕴的厚度、视野的广度、思想的深度,这恰好和诗人的人生阅历、知识积累形成了一种正向的对应关系。向深处挖掘是吴海歌近年来诗歌探索的一个重要向度。在这个年龄,他的思想没有僵化,思维没有模式化,无论是打量历史、现实,还是感悟人生、生命,他总是尽可能摆脱表面的观感,尽力抓住历史、现实、生命中的普遍性内涵,抒写他所感悟的人生哲理。于是,我们见到《绘画者》有了特殊的魔力:“她的手,曾经握住过什么/肯定不是画笔,也不是平淡的庸常生活/难道是闪电,从骨头里迸发/是撞击,从粉碎中/被她握住”,超越了庸常生活,感受到了闪电、骨头,而且是向死而生的那种力量,从粉碎中获得新生。 诗歌创新的路径很多,可以来源于独特的阅历,丰富的想象,别样的语言,深刻的思想,也可以来源于超越常识的发现……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给诗歌带来新意。当然,如果能够在多个方面都体现出独到之处,这样的诗就可以更好地展示出诗人在艺术上的辨识度。吴海歌近年的诗歌写作,在这些方面都有所体现,但更为明显的是他在思维方式上的转变。 反思,成为他诗歌探索中的亮点之一。这种方式,非常适合具有丰富阅历的年龄阶段。丰富的阅历业已定型,人生旅途上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他观照的对象。他并不是顺着常态的思路去回顾,而是对经历的一切、面对的一切、思考的一切,都进行多侧面思考,尤其是以反思的方式去打量,由此获得和过去、和他人不一样的诗意发现。《关于声音》中的“声音”,可能是真正的声音,也可以看作是诗人的吟唱,但它确实是不一样的“声音”:“我说的声音不止爽心、悦耳/不止朝向一人一物。不止柔软/我说的声音,不是常识的声音//不仅来自美妙的歌喉/也来自狂妄与意念,匕首与黑暗/仇恨与对抗,暗示与香/带有欲望和意图的色彩//我说的声音,或许是子弹/冲击波,放射物/某种针对病灶的靶向药”,诗人试图避开“常识的声音”,在“声音”中加入了反思的意味,甚至加入了讽刺、批判和用于精准治疗的“靶向药”。我个人从这种味道之中感受到了一种担当、一份情怀,使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历史、现实与人生,使我们在“爽心、悦耳”之外,获得对人生的更丰富的认知。 当然,我并不认为海歌兄的探索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完美。或许是在思维上形成了某种新的定式,他的有些作品在呈现方式、话语方式、文本结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同质化倾向,只是换了场景,换了意象。在这方面,海歌兄投入了很多精力,他试图通过自我回望,避免思维方式的重复化、同质化。 在诗歌界,有些诗人和学者按照诗人的年龄及其作品的艺术特点,提出过青春写作、中年写作、老年写作等概念。吴海歌的这部诗集恰好是他六十岁之后的艺术收获,在年龄上介于中年写作和老年写作之间,该书的出版也将他带进了古稀之龄。可以看出,他对人生的感悟、思考,他的诗美发现、表达,似乎并没有老化之感,而是用一颗赤诚之心,反思曾经走过的路,具有浓郁的批判意味。“内视镜”这个名字用得不错,是诗人对自己的人生与创作的一次新的探索、向内的探索。这是诗人由中年写作转向老年写作的一种预演,在那之后,海歌兄诗歌中的回望、重审、反思元素就越来越多,逐渐进入到另一个创作时期。 我相信,一个真正爱诗之人不会停下对诗歌艺术的探索。不过,我们又必须承认,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每个人都会在诗美感受力、语言敏锐性等方面逐渐出现钝化的情形。面对这种变化,如果还要继续写诗,诗人就有必要转换切入方式,另寻他途,比如在拓展深度、扩大视野等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我们期待他在诗歌的“老年写作”中为我们提供更多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本文系西南大学教授、重庆市作协副主席蒋登科教授为吴海歌诗集《内视镜》撰写的序言,该书已于2024年6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报刊发时有删节) 来源:重庆晚报 | 选稿编辑:牧 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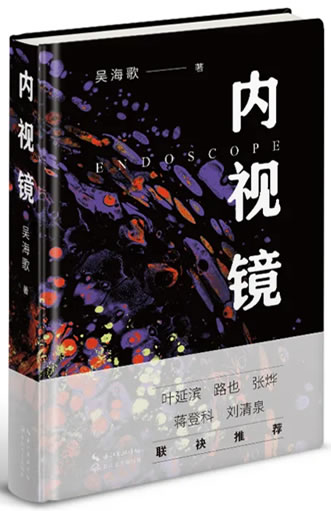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