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平: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听觉段位"的隐喻性叙事
杨四平,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华夏文化促进会顾问、香港文学促进协会顾问,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 在西化文法催生下,现代汉诗出现了许多古代汉诗里所没有的新段位。现代汉诗叙事的段位从来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它们使用简体字、新词语、长定语、后置附加语以及追加式和插入式的叙述方式与横排格式等。它们不是形式主义意义上的装饰品!它们将诗的声音与含义融为一体,成为诗本体的有机构造,体现了现代汉诗段位叙事的现代性。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的叙事段位,既有显而易见的标点符号、字词、短语、诗行、诗句、诗节和诗章这些文字符号层面的段位及其空白,笔者将其称之为“视觉段位”;也有看不见的、但对现代汉诗而言极其重要的韵律之类的诗歌声音,笔者将其称之为“听觉段位”;前者是由各种视觉段位及其排列生发的“音响性叙事”,后者是由各种听觉段位及其声音序列生发的“隐喻性叙事”;而且,前者的单位大小依据后者的长短、轻重和缓急来划定,也就是说,后者对前者具有决定作用。本文将探讨现代汉诗的听觉段位及其生发的隐喻性叙事。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主张用音乐来思维,用音乐来传达。魏尔伦在《诗艺》一诗里写道:“音乐先于一切”。其实,诗歌叙事既关涉语义学,又离不开语音学。现代汉诗向来重视“意义”,忽视“声音”,存在重“意”轻“声”之弊端,显得“质感”有余而“乐感”不足。然而,好诗应该是“意义”和“声音”之间的无缝对接,和谐共生。而诗的“声音”既指显在的符号和文字,也包括隐在的韵律。质言之,诗中的声音,既指诗中标点符号、字、词、句、行、节、章及其排列所产生的音乐;又指隐喻意义上的声音,关乎诗的韵律和魂魄,昭示诗的某种品质。前者就是笔者在上一节讲到的音响性的诗歌声音叙事,后者是本节笔者即将要谈到的隐喻性的诗歌声音叙事。艾略特曾经把诗的声音分为三种:“第一种声音是诗人对自己说话的声音——或不对任何人说话时的声音。第二种是诗人对听众——不论是多是少——讲话时的声音。第三种是当诗人试图创造一个用韵文说话的戏剧人物时诗人自己的声音,这时他说的不是他本人会说的,而是他在两个虚构人物可能的对话限度内说的话。”[1]显然,艾略特谈的是隐喻意义上的诗歌声音。它们依次是诗的抒情声音、叙述声音和戏剧声音;换言之,它们就是诗的独白、宣叙调和戏剧对话。 《艾略特诗选》书影 诗中抒情的声音,虽说总体上是抒情,但也内蕴着叙事的因子。郭沫若的《炉中煤——眷恋祖国的情绪》,按照副标题提示,全诗抒发的是诗人对祖国的眷恋。它先是用“炉中煤”比喻“我”对“年青的女郎”的挚爱,再用“我”对女郎的爱比喻“我”对祖国的爱。这首抒情诗的叙事线索是,由自然之爱,述及男女之爱,最后升华至诗人对祖国的爱。伴随着这种自然之爱——小爱——大爱的递进,诗的声音由自然产生,渐次洪亮,直至高亢。五四时期这种启蒙性的黄钟大吕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革命进行曲所取代。诗中的叙述声音得到不断增强。它响彻了整个三、四十年代。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中国诗歌会诗人、左联诗人和抗战诗人大声宣称,诗歌是匕首、炸弹,诗歌是口号、旗帜;从殷夫的《血字》到田间的《给战斗者》,都发挥了开辟文化战场、鼓舞革命士气的政治作用。它们不是个人呢哝,更非个人呻吟,而是集体大合唱、进军号角。在这种时代宣叙调之外, 三、四十年代还出现了另外一种诗歌声音,那就是戏剧化对话。从三十年代的卞之琳到四十年代的穆旦,现代汉诗里既容纳了时代潮音又不乏个人独特的声响,使得他们的诗歌成为那个时代难能可贵的“多声部”。 其实,现代汉诗声音诗学的丰富实践,远远超出了艾略特所划分的三种声音。也就是说,艾略特将诗歌声音划分为三种尽管有统揽全局的气魄,但仍不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现代汉诗声音诗学的真正魅力。笔者认为,对于现代汉诗声音叙事的分析宜细不宜粗。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影 《凤凰涅槃》是一曲关于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火中更生的诗歌喜剧。从音乐段位上划分,它依次有以下几个段位:序曲、主曲(“凤歌”“凰歌”和“凤凰同歌”)、变奏曲(“群鸟歌”)和髙潮曲(“凤凰更生歌”)。我们通常将其解读为历史青春期的时代颂歌。郭沫若独步五四,雄姿豪迈。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西方人文思潮影响,国内开始出现否定郭沫若的思潮。而这种“倒郭”思潮恰好又与海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遥相呼应。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把冰心与郭沫若相比,以冰心的“零碎的思想”“片断的思想”“短小的、静谧的、克制的形式”,否定郭沫若的“好为大言”,“对现实世界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并否弃”,“用最高级语式召唤即将到来的永恒时代”,“冗长的、高分贝的、直白的形式”。[2]现今,有些学者认为,西方汉学家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评判是以西方意识形态反对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这种“冷战”式的对抗思维使得他们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现代中国文学。非此即彼不是常态,两种或者多种诗歌声音是可以同时并存的。 现代汉诗史上,像《凤凰涅槃》这样如此明显、如此完整、如此丰富的诗歌音乐段位结构是罕见的。尽管不少叙事长诗试图以类似庞大而完整的音乐段位来组织材料,提炼主题与完善架构;但是成功的范例并不多见。在笔者的现代汉诗知识体系中,它们之中成功的典范似乎只有两篇活用民歌体完成的叙事长诗——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和阮章竞的《漳河水》。因篇幅所限,这里仅以《漳河水》为例来谈谈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民歌体”的诗歌段位与叙事段位之关联性问题。“作品刻画了三个妇女形象:荷荷、苓苓、紫金英。荷荷勇敢、苓苓机智、寡妇紫金英则较懦弱。她们性格不同,但最终殊途同归,都走上了争取幸福的道路”[3]。全诗由《往日》《解放》和《长青树》三个部分组成,以常见的新旧对比、新中国成立前与新中国成立后对比、人物性格及命运的前后变化为主导的革命写实叙事模式,佐以人物的多重对照和总分的戏剧化结构,既表达了宏大主题,又避免了单调呆板。“戏剧化结构、多种歌谣形式解决的是叙事诗歌的大框架问题,阮章竞还解决了叙事诗大结构和小细节的融合问题、叙事性跟民歌体式相融合问题、诗歌篇幅有限性跟多线人物的复杂性相协调问题、讲故事与塑造人物的问题、写景与抒情的结合问题、诗歌如何进行心理描写问题。必须承认,在一首诗中把所有这些问题都解决并非易事,然而《漳河水》却进行了努力的尝试,并且成功了。”[4]为了使这个故事讲得生动、形象、感人,阮章竞借鉴了流行在漳河一带的《开花》《四大恨》《割青菜》《漳河小曲》《牧羊小曲》等民间小曲,仅第三部《长青树》就由“漳河谣”“翻腾”和“牧羊小曲”三组套曲组成;换言之,阮章竞是根据情景变化、基调明暗和情节起伏来取舍诸种歌谣,杂采成章,形成了歌谣的“大杂绘”;但是,为了更利于表达主题、传达情感,使大众喜闻乐见,阮章竞对它们进行了加工,最终形成了拟歌谣体的文人诗。 作为优秀的现代汉诗,自身音乐的完整性是最起码的要求;只不过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它们有的显在,有的隐匿;有的丰富,有的单纯…… 李金发 现代汉诗中的三部曲,也是一种完整的诗歌音乐段位结构。徐志摩的散文诗《命运的逻辑》,用“前天”“昨天”和“今天”串起声音三部曲和命运三部曲。全诗用了一个整体比喻,把命运比作一个女人:青春期(“前天”),天真无邪,激情奔放;中年期(“昨天”),追名逐利,出卖灵魂;老年期(“今天”),令“神道”“摇头”,使“魔鬼”“哆嗦”。命运由青春而坠向暮年,由美好变为丑陋。诗的声音也随之由激越渐渐降至低沉,再由低沉升至诅咒。这既是命运演变的逻辑,也是诗歌声音变奏的逻辑。 现代汉诗草创期,不止是浪漫抒情诗歌不注重诗歌音乐性,就是写实性叙事诗歌也是如此(如刚才谈到的《漳河水》);而呈现性叙事诗歌更不在意诗歌音乐性,尤其对于那些徒有外在标识的音乐性更是不屑一顾。李金发说:“我做诗全不注意韵,全看在章法、造句、意象的内容”。[5]正是由于草创期现代汉诗普遍不重视诗的音乐性,致使其出现了伪浪漫、伪感伤的通病。 新月诗派提倡现代格律诗理论及其实践,为拯救现代汉诗于危难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由此,现代汉诗诗坛还发生了一波波的现代格律诗论争,成为现代汉诗声音探索和实践中影响甚巨的事件。最重要的理论文章是闻一多的《诗的格律》。闻一多要求现代汉诗必须做到“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6]。它们几乎是从古代汉诗理论那里转化而来的,尤其是从前面“两美”里可以看到“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7]的影子。当然,这其中也不乏西方唯美主义诗论的影响。新月诗派最重要的代表作品除了前面提到的《再别康桥》和《雨巷》外,还有《死水》和《采莲曲》。《死水》里诗人的愤激和诅咒之情,在象征和反讽技术的牵引下,通过“三美”的处理和转化,没有成为脱缰的野马,没有变成直白的口号;而是被牢牢地控制在诗歌音乐表现的理性范畴之内。“诗句欲雄壮不难,雄壮而有绵至之思为难,故外强中干,诗家切忌”。[8]全诗每节四行,每行九个字,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七言古诗的九言长方形诗体;各行都是四顿,由三个“二字尺”和一个“三字尺”构成,开头和结尾均是“二字尺”,且都以双音节复合词收尾。质言之,在一行之内,闻一多采用了西式轻重律和长短律,通过它们之间的协和来完成一行里的韵律结构。如果说这些体现了现代汉诗“音乐的美”和“建筑的美”,那么诗中的否定性意象“破铜”“烂铁”“剩菜”“残羹”就体现了现代汉诗的“绘画的美”。以往,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音节”,“建筑的美”常常包含于其中隐而不显;而对于“绘画的美”谈得很少,因为当时人们很少注意到“词藻”对于建设现代汉诗格律的意义。其实,如果从语义上讲,首节就已经婉曲地叙述出了“索性让‘丑恶’早些‘恶贯满盈’,‘绝望’里才有希望”[9]的主题。读者也不难品味到“强烈的恨”下掩藏着“绝望的爱”。从这个角度看,其他诗节作为它的“复调”,只是在不断变化的旋律中,强化这一主题的深入表达。在那个礼乐尽失的惨不忍睹的时代,在诗歌写作中追求和展示独立、整饬、和谐与完美,依然是作为一位中国现代诗人对那个时代最佳的美学回答。此乃波德莱尔所言“恶之花”的美学政治:在貌似回避现实叙述中,仍然曲折地关心着社会变革。朱湘的《采莲曲》以“形式的完美”“文字的典则”和“东方的静美”[10],殊途同归地创造了又一首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经典。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也只例举首节:“小船呀轻飘,/杨柳呀风里颠摇;/荷叶呀翠盖,/荷花呀人样娇娆。/日落,/微波,/金丝闪动过小河。/左行,/右撑,/莲舟上扬起歌声。”朱湘说:“天下没有崭新的材料,只有崭新的方法”。[11]根据他在不同场合的各种各样的表述,综合起来,可以得到朱湘做现代汉诗的“崭新的方法”有:注重情与景、物与我的统一;用字的新颖与规范;用韵严格且要与诗的情趣相协调;诗体形式要独立、匀配、紧凑、整齐。总体来看,朱湘是在现代格律诗中复活了诗、画、乐一体的古典传统。刚一接触此诗,回响在我们耳畔的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再细读下去,又能从“日落/微波/金丝闪动过小河”听到苏轼《调啸词》的历史回响。具言之,如果从诗与画方面讲,全诗先后展示了“溪间采莲图”“溪头采藕图”和“溪中采蓬图”,最后共同构成一幅“江南采莲图”的总图。其实,它也勾画了先在溪间采莲,接着在溪中采藕,最后在溪中采蓬的叙事历程。如果从诗与乐上讲,朱湘在这里践行了考德威尔所说的诗乐之共同理想是美。因为考德威尔认为,“诗的幻象”就是“诗永远渴望变为音乐”。[12]具体来说,朱湘化用了“长短句”的诗词格律,每节韵式整齐中有变化,变化中又不失规律,且押“人辰韵”。这种先重后轻的韵律,奇妙地传达出了采莲小船在水面滑行时,随波轻晃的情韵。质言之,此诗的叙事段位与诗歌段位之间对位熨帖。它的现代性在于:对纯语言、纯形式的意愿及其音乐方面的唯美主义体现,还有那不经意间表露出来的古典主义倾向。 《闻一多全集》书影 复调与变奏也是现代汉诗常见的音乐形式。前面说的《死水》可以作如是观。下面,请读孙毓棠的《踏着沙沙的落叶》: 踏着沙沙的落叶, 唉,又是一年了,秋风! 独自背着手踏着 沙沙的落叶;穿过疏林, 和疏林的影,穿过黄昏。 黄昏静悄悄的,长的 是林影。沙沙地踏着, 踏着,是自己的梦, 枯干的。又一年秋风 吹过了,自己的梦。 看枝头都已秃尽了, 今年好早啊,秋天! 年年在白的云上描 自己的梦,总描不团圆。 描不整,描不完全。 等秋风一吹,便随黄叶 沙沙地碎落了。秋风早, 只好等明年吧。 看秋风吹白了野草, 吹得凄凉,吹得老。 踏着沙沙的落叶, 唉,又是一年了,秋风! 独自惆怅着,在落叶上 走;穿过疏林,和疏林 淡淡的影,穿过黄昏。 这首诗所叙之事很淡,情也不浓;整整五节,仅仅叙述了叙述者在一个秋日黄昏,独自踏着落叶,感受着梦境与凉意。这多少会让人想起理查德•克莱德曼弹奏的钢琴曲《秋日私语》。沉思者内心里的低吟与长叹,其实,在首节诗里就已经通过迂回、重复和缠绕的表达方式大体得以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其余各节都是对它的复调和变奏,尤其是末节,几乎是首节的复现,营造了变奏与叠唱共生的音乐效果。音乐最重要的品质就是重复和变化,在重复中变化,在变化中重复;其中,通过大量在句末和行中使用标点符号造成的停顿以及跨行形成的跳跃,加上韵脚“en”“eng”“an”“ao”的不断变换,使得全诗音乐不再单一,反而变得丰富起来。这种音乐性,与传统意义上的格律不同,后者是辅助性的、装饰性的、事先就有的;那样的格律只能导致诗歌写作意象的集约化、句法的淡漠化和诗节的板结化。诗人写作应该尊重语言自身的本性。在我看来,理想中的诗歌语言其实是一种“自然”语言。当然,在非现代主义诗人看来,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虚幻性。而我们从孙毓棠的这首诗里反证了此种说法的虚幻性,因为它的音乐既看得见,也听得见! 《今日评论》书影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诗歌的音乐很深邃,很邈远,难以听见。1937年3月到5月,卞之琳写了5首“无题诗”。请读这年4月他写的《无题二》: 窗子/在等待/嵌你的/凭倚。 穿衣镜/也怅望,/何以/安慰? 一室的/沉默/痴念着/点金指, 门上/一声响,/你来得/正对! 杨柳枝/招人,/春水面/笑人。 鸢飞,/鱼跃;/青山青,/白云白。 衣襟上/不短少/半条/皱纹, 这里/就差/你右脚——/这一拍! 首节叙述的是:叙述人在室内“等待”“你”、“怅望”“你”;就在这焦急的、枯寂的、痴情的等待和怅望中,突然听到“你”的敲门声;叙述人由衷地发出感叹:“你”来得正是时候啊!末节叙述的是:当叙述人打开大门迎接“你”这位贵客的时候,所见到一切,所感受到一切,如沐春风,有了春天重临人间的感觉,一句话,有了重生的感觉(第一、二行用场面来暗示);当叙述人从亢奋中缓过神来后,仔细端详久违的“你”,发现“你”还是预想中的“你”,丝毫不差!如果说眼下“这里”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么就差“你”抬起右脚跨进室内了!这是从语义层面上来说的。如果从语音层面上看,此诗每节四行,押交叉韵;每行十个字或十一个字,“二字尺”和“三字尺”交替着使用。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作为收束全诗的“这一拍”,是内容和形式上的双关。对此,当年卞之琳把自己的诗集《十年诗抄》送给废名时,曾专门就此做了解虽然所等之人“右脚已到了 ”,但是“诗的韵律”还“差一拍”。[13]具体来说,从内容上看,“一室的沉默”都在等待“你右脚”,等待“你右脚”进来打破“一室的沉默”,恢复这里的生气和活力。从形式上看,因为整首诗每行都是四顿,末节也在等待“这一拍”才能完满。这种韵已经完全不同于古典诗词的格律,而是一种内在音乐性。值得补充的是,“这一拍”也是卞之琳富有创意地将古典诗词的“三音尾”化用于此。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双关的巧夺天工,也许是由于卞之琳诗歌一贯的联想繁复、暗示浓缩、运思玄妙和观念跳脱,所以,他把此类诗取名“无题”。由此可见,卞之琳写诗之智性、痴情与功力。 《文艺月刊》书影 当然,现代汉诗史上曾经有人热心为现代汉诗制造“新模子”;然后,再往这种自制的“新模子”里“填词”。这里举个极端的例子。1928年11月《乐群》半月刊第4期发表了陈启修的《有律现代诗》,提出诗歌必须有韵律;没有韵律的诗,只能是“可看的东西”而不能成为“可吟的东西”;所以“应该在诗的形态上研究,去造成诗的韵律,一面要用‘相关韵’的脚韵,一面要确定每首诗每一句的音数和逗数,标在诗题的下面。(如3/14为十四音三逗诗,2/14为十四音二逗诗)以示这首诗的格局”[14]。按照他的理论,就是一个字一个“音数”,一个逗号一个“逗数”;整首诗的音数与逗数需“确定”。他本人的《飞鸟山看花3/14》就是这种理论的实验品:在8行诗中,每行都有用3个逗号隔开的“逗数”;除第7行为13个字外,每行均为14个字,也就是说,只有一行诗例外,其余各行都是14个音数。如果按他的这种理论,像《死水》和《采莲曲》这样优秀的现代格律诗都不合格。难怪,1929年3月3日在《海风周报》第9号发表祝秀侠的《评陈勺水的有律现代诗》,对此提出质询,并引发了一直持续到30年代中期的“有律现代诗”的诗学论争。 《朱自清全集》书影 笔者丝毫不怀疑这类诗人对现代汉诗音乐性探索的真诚,完全理解他们建设现代汉诗形式的热情。笔者认为偶一为之,实验实验,无伤大雅;但对他们那种过激的言论与偏执的行动应持批判态度。没有固定的形式,不重视诗的声音,的确是现代汉诗为人诟病的原因,也是导致现代汉诗写作乱象丛生的根源之一。但是,我们是不是反过来想想,没有固定形式(但必须要有形式感和形式意义)恰恰就是现代汉诗最主要的形式。不注重诗歌外在音乐性并不意味着就不重视诗的内在音乐性;毕竟现代汉语的语音是辅助性的,句法是散漫的。现代汉诗与古代汉诗在语言上的区别十分明显。古代汉诗使用单音节的具有完整意义的字,通过平仄来调节,把助词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使得诗体严整、简练、短悍到了极致。而现代汉诗极少用单音节的字,替代它们的是双音节和多音节的复合词,如“冷漠”“凄清”“又惆怅”“轻轻的”“悄悄的”。捷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说:“在汉语中,只有有重音的字词才发出清晰的字调,而非重音的字词的发音只是陪衬整个句子的韵律色彩。中国诗句正由音调的和谐转变为重音作诗法,在这方面中国的新诗正逐渐向欧洲的诗,包括捷克的诗接近”。[15]现代汉诗不是靠平仄来调节节奏,而是听凭情绪节奏的轻重缓急来组织。诗无定式,诗无定律,恰恰就是现代汉诗最初追寻的梦想。笔者想,诗人们要做的事情是,如何根据自己的写作个性,尽量做到所写题材与所选形式及声音之间保持最大的适切度;不要先给自己定一个模子,或者说给自己一生的写作制定一个模子或若干模子;更不能将其强加给别人,何况那种一厢情愿注定是徒劳的。 《沙扬娜拉》图影 其实,现代汉诗的音乐性不是装饰性的,而是伴随着题材,随着诗人对题材的个性化处理,随着字词行句、标点符号和书写形式“一起到来”。也就是说,现代汉诗的音乐性是“与诗倶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有“诗不可译”之类的说法。这种翻译不仅指不同语种之间互译,也应该指同一语种内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之间互译;具体到现代汉诗而言,这种翻译既指将现代汉诗与外文诗歌之间互译,也指现代汉诗与古代汉诗之间互译。徐志摩的《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脍炙人口:“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一/沙扬娜拉!”当代诗评家江弱水为了说明最终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因素而不是英国浪漫主义造就了徐志摩诗歌“在读者接受方面上的成功”,至少是为了说明《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将“古典情韵与异域情调结合得相当好”,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后者改写(翻译)成一首极具苏曼殊式哀婉艳情的绝句:“最是温柔一低头,凉风不胜水莲羞。一声珍重殷勤道,贻我心头蜜样愁。”[16]两相比较,优劣分明。当然,值得肯定的是江弱水将现代汉诗戏仿成古代汉诗的雅趣。改写后的绝句难以传达出原诗的情调和韵致。最初的《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有18节,夹杂不少日文,且平声过多。修改后,压缩为一节,而且将“睡莲花”改成“水莲花”,将“寒风”改成“凉风”。针对该诗的用字以及后来的修改,金克木在《读书》1991年第11期上发表《“寒”“凉”有别》,认为唯有用凉风吹花方能贴切地传达出日本女子待人接物时,尤其是在与客人道别时的娇羞柔情与“蜜甜的忧愁”。[17]徐志摩将“寒”改“凉”,对日本女郎道别时的心态、情态、神态、语态乃至体态,以及诗人对其怦然心动,得以完美呈现。如果从叙事角度来讲,全诗仅仅描述了日本女郎在向客人道别时,边“低头”边说“沙扬娜拉”的情景。如果用散文来叙述,便兴味全无。正是由于徐志摩将诗歌段位与叙事段位完美结合,才写出了如此令人爱不释手、反复吟诵的诗篇。一上来就用“最是那”起首,用最高级的词汇表达,就是想一下子吸引读者的注意,抓住读者的心。然后,在“头”“柔”“羞”三个字的重复“尤”韵中,“一朵水莲花”般清纯可人的日本女郎登场了。随之,在接二连三、轻声细语地道“一声珍重”里,诗人分明感受到了世界上最难得的、弥足珍贵的“蜜甜的忧愁”。而破折号的使用又延缓了诗人享受这种姿态、这种声音和这份情感的过程。真的不忍心“沙扬娜拉”,但毕竟“沙扬娜拉”了。诗人写下这首《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就是要将其保存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一个小小的举止,一声轻轻的道别,诗人就能从中品味出一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情感故事来,足见诗歌写作,不仅需要经验,也需要体验,更需要想象力和表现力。试想,如果将“沙扬娜拉”改成“再见”,将“道”改成“说”,将“蜜甜”改成“甜蜜”,而且,继续用“睡莲花”“寒风”,那么这首诗的品质将会大打折扣。进一步说,只要改动其中任何一处,这“一字之差”“一音之别”都会给人“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感觉,更何况全面译介乎!朱自清说:“一切翻译比较原作都不免多少有所损失,译诗的损失也许最多。”[18]的确,对于原诗而言,译诗往往面目全非、吃力不讨好。叶公超当年曾告诫:“严格说来,译一个字非但要译那一个而已,而且要译那个字的声、色、味以及一切的联想。实际上,这些都是译不出来的东西”。[19]可见,诗歌段位的重要性和不可更改性。每一首诗的诗歌段位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赴德留学的冯至反思自己早年写诗的经验时表示,如有可能,他要从“小学”[20]学起,要从蕴含着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的汉字及文法里汲取智慧。像冯至这样的现代主义诗人,到后来才娴熟地驾驭西化式的反讽、叙述、独白等声调和语调,短句与长句交错,句式与场景对照,意象与场景叠加,形成立体乐感与多重声音。 英国诗评家K·M·威尔逊说:“我们可以像欣赏纯音乐那样地去欣赏诗,我们可以把诗的意义完全撇开,而仅仅作为一种美的、印象深刻的声音的连续而去欣赏它”。[21]如果我们不全盘照搬他的思想,而只是将其视为对诗歌声音的“提醒”,在写作与欣赏中不要将其遗忘;那么我们就能从中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真知。笔者认为,现代汉诗不同于古代汉诗的重要一点,就在于后者的声音没有“意义”,而前者的声音是有“意义”的声音;总之,在现代汉诗中,声音是有意义的声音,意义是有声音的意义。 《古代诗话提要》书影 总之,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叙事的诗歌段位,既有文字和符号层面的显在的诗歌段位,又有韵律及其灵魂层面的隐在的诗歌段位;如果说前者是某种视觉段位,那么后者至少就是某种听觉段位。为什么说是“至少”呢?是因为它拥有其他声音所没有的魔力。而这种独特的声音魔力除了来自诗歌段位及其排列所造成的声音外,还来自其渊源有自的隐喻;正是有了这种文字段位和符号段位背后的声音魔力使得诗歌的文字段位和符号段位也具有同样的魔力;换言之,诗歌的文字段位和符号段位的魔力源自沉潜的诗歌声音段位的魔力。前者取决于后者,后者“给定”前者。如果说前者是肉体,那么后者就是灵魂;只有二者合二为一,方能完成一首诗的叙事,才能成就一首完整的诗篇。 《当代西方美学》书影 行文至此,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本课题所预设的任务了,该是收束全文主体论述的时候了。既然笔者一贯认为,对于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叙事而言,现代性是其统摄,段位性是其归结;那么,我们可以仍然以此来收揽全文的主体论述。笔者认为,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叙事形态的形成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文学史意义:第一,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叙事形态是“新”的,在古代汉诗里几乎找不到它们的踪影;而这种“新”在精神文化层面与现代性相通。正如王富仁所说,即使“‘现代性’的观念与古典的、经典的、传统的观念也是交错、交织在一起的”;但它们“到底还是冲破了中国固有的古典的、经典的、传统的观念的束缚和禁锢而进入到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之中,并在总体上改变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22]质言之,对现代汉诗写作而言,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叙事形态具有打破古代汉诗写作的禁锢与困局、开辟诗歌写作“新时空”的方向性意义。第二,从段位性的角度来看,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的叙事段位有视觉段位、听觉段位及其隐喻段位,换言之,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的叙事段位具有视觉性、听觉性和隐喻性,尤其是其隐喻性,是小说、散文和戏剧等非诗文体的叙事段位所不具备的,申言之,是隐喻性将诗、画和乐“合三为一”,使得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的叙事段位具有其他文体、乃至现代汉诗的抒情与议论所无法比拟的综合性和丰富性。由此,我们可以说,诗歌叙事的段位性,是视觉性、听觉性和隐喻性兼具的诗歌特性。而这种诗歌特性既具有由语言原始的诗性隐喻带来的自述功能,又拥有因其所处的特殊历史语境而显示出来的逻辑分析性;正是这种自述性与分析性的结合使得现代汉诗段位叙事成为可能,并且具有现代性特征。第三,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叙事的现代性与段位性是共生的。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叙事的语义学与语音学的充分熔冶,促成了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叙事从开初的蹒跚学步到最后的健步前进,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写实叙事、呈现叙事和事态叙事的现代诗歌写作体系,提供了中国现代抒情诗和中国现代智性诗所无法提供的新经验、新景观,部分地刷新了现代中国诗歌,乃至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第四,借此我们也明显看到了现代汉诗的历史性进步。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在于:诗人完全拥有对语言的取舍权,抛弃任何诗歌的成规,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才能、禀赋和意志。一言以蔽之,现代诗人可以自由拥抱语言。如此一来,现代诗人既解放了语言,也解放了自己,更解放了诗歌。此前,诗人们一提笔写作,那些固有的字词、短语、句子、典故、意象和技法就蜂拥而至、麇集笔端;在此情境下,有的诗人难以下笔;有的诗人虽然勉强硬撑着写,但那也是一种模拟性或仿古性的写作,了无生趣。本来,诗歌与叙事、诗意与散文之间具有天然的难以化解的矛盾。但是,对于现代汉诗而言,这种矛盾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它总是激励着诗人们迎难而上,进行自由创造,并在艺术创造中尽享诗歌写作带来的自由。而正是这种自由的探索与探索的自由将伴随现代诗人迈进新的历史时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诗的叙事形态研究”(项目批准号:15BZW123)的阶段成果。本文原刊《中国诗学研究》第12辑,引用请以原刊为准。 《二十世纪中国新诗主流》书影 [1]T•S•艾略特:《诗的三种声音》,《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94页。 [2]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3]阮章竞口述,方铭执笔:《异乡岁月•太行山》(未刊稿),1989年7月。 [4]陈培浩、阮援朝:《阮章竞评传》,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页。 [5]李金发:《诗问答》,载《文艺画报》第1卷第3号,1935年2月15日。 [6]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诗镌》第7号,1926年5月13日。 [7]阮元:《文韵说》,顾俊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册,台湾木铎出版社1981年版,第285页。 [8]乔亿:《剑溪说诗》卷下,赵永纪编《古代诗话精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39页。 [9]朱自清:《朱序》,《闻一多全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页。 [10]沈从文:《论朱湘的诗》,《文艺月刊》第2卷第1期,1931年1月15日。 [11]朱湘:《朱湘书信集.寄赵景深》,天津人生与文学社1936年版,第53页。 [12]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黄梅、薛鸿时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13]废名说“作者送我一本《十年诗草》的时候,曾把这首诗指给我看,生怕我不懂最后一行破折号后面的‘这一拍’,他说‘这一拍’的地位是所差的右脚已经到了,诗的韵律虽差一拍,而人到了。”(冯文炳:《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14]勺水(陈启修):《有律现代诗》,《乐群》(半月刊)第4期,1928年11月。 [15]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丛林、陈平陵、李梅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16]江弱水:《中国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丛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17]金克木:《“寒”“凉"有别》,《读书》1991年第11期。 [18]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71页。 [19]叶公超:《论翻译与文字的改造一答梁实秋论翻译的一封信》,《新月》第4卷第6期,1933年3月1日。 [20]冯至:《〈萨拉图斯特〉的文体》,《今日评论》第1卷第24期,1939年。 [21]参见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7页。 [22]王富仁:《“现代性”辩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供稿:原作者 | 责任编辑:牧 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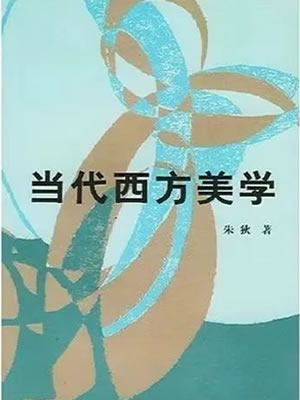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