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大运河的诗意故事和人事
《水调歌头》:大运河的诗意故事和人事 李继豪 2022年6月,胡弦的长诗《器识》发表于《诗刊》,诗后附有一篇题为《踪迹》的创作谈。在文章结尾,胡弦谈到:“《器识》,是我正在写作的运河系列诗歌中的一首。这个系列主要由小长诗组成。我把中国水系看作连通中国精神的一个装置系统。我一边写一边能体会到,我对一条河的情感,包含在从现实场景中直接获取的物象里,也包含在所有失踪的事物中。河流本身不再是写作唯一的着力点,我要的,会从一种更宽广的视域和更长久的意义中显形。”如今,诗人所预告的运河系列诗歌都已收入《水调歌头》这部诗集中。也正如诗人所描述的那样,“河流”并非写作的“着力点”,而更像是一个“起兴”的源头,隐现在“水调”中的纷繁故事与隐秘人事则构成了诗歌绵密的肌理——数千年的交通史、农耕史、文化史随着一个物象的打开、一页典故的演义复活在现代汉语的诗行中,时代的滔天巨浪与个体命运的细小浪花随着一场行迹的变迁、一次记忆的寻访重新由时间之海翻卷回语言之岸。 《庇护》是这部诗集的开篇之作,它试图通过对旧时间秩序的回溯与整理捕获那种被命名为“庇护”的原始力量。这种“庇护”并非来自诗人有意为之的提纯与想象,而是在故事与人事的娓娓道来间呈露出真实可触的质地:“这就是庇护:光线从窗格里射进来,/岁月,是镂出花纹的空气。/炕,靠着山体,像靠着牢不可破的安宁。”而现实中的我们不得不接受曾经的居所废弃后的样子——它空荡荡的、成为了杂物间的样子。当那个捧着家谱的族老风尘仆仆地来到诗人面前,在喧嚣匆忙的城市生活的“另一种庇护”的对照下,诗人牢牢记住了他“像个流浪的、最后的家神”般“灰扑扑的身影”。尽管那份独属于乡土中国的“庇护”在结构和形态上已经濒临坍塌,但那些杳然而去的和正在上演的故事与人事却时刻建筑着新的“庇护”:村庄的环装形制、恋人依偎的甜蜜背影、高大的围墙、书桌上老砖头磨成的砚台……具体而坚实的物象跃动在记忆与现实之间,时刻提醒着一种古老、安宁而永远不会真正失去的生活。 “当船在河里航行,/我们的石头也在水中赶路。”在《压舱石》这首诗里,河流让时间的流逝有了更为明晰的刻度,唐德宗的绝处逢生、刘禹锡的才情挥洒、文天祥的碧血丹心都被一条大运河所映照和记载。在写作层面,这首诗还揭示了一个被小说家奉为圭臬却常被诗人搁置一旁的道理:人事是故事的灵魂,一切故事不过是人事的行迹。诗中,小镇的故事,史书里的故事,友人的故事,诗人童年的故事背后皆为人的悲欢离合、进退行止。游离于一切叙述之外的压舱石,时而进入军阵、城门、山岳、人格、心灵等一切盛大庄严事物的阴影之中,时而又溜进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日常物什之列。而正如它的形体般沉重的意义在于,面对一条时光之河的变动不居,这块从未出现在博物馆的压舱石,终是做了一切故事与人事最忠实的见证者。“猛浪若奔,它默而识之。/流水无情,它默而识之。”一块压舱石,沉默、稳固、亘古如斯,恰如语言本身。与《压舱石》这首诗类似的是,诗集中的大部分诗作都拥有一个中心物象,有博物馆中残损的陶罐,“一处/我们遗失在时间中的住宅”(《器识》),有流芳百世的清明上河图,“一张画仿佛/一代代人无法完成的旅行”(《画卷录》),亦有一轮江都的月亮在古与今、戏与真之间浮动,“一张缺口的口,/吃掉了年代间漫长的距离”(《江都的月亮》),还有一块只存在于祖父的讲述中的醒木,诗人眼中那个“无解的声音”,“他说,好的说书人都知道,醒木,/比故事本身更重要:故事可以修改,唯有/醒木那啪的一声无法修改”。(《醒木》)不同于古典咏物诗中的“物”,胡弦诗中的物象不着眼于象征意涵的过多延伸,而着眼于诗人所见所历的故事、人事与物象之间的自然关联。这种关联无须过多借助于外在的飞驰的想象力和精致的修辞术,而是深深根植于诗人关于情感、知识与经验的内向启示。因其情感、知识、经验的丰富和多维,因其“内向启示”本身的“内向性”,《水调歌头》中的诗歌在面对一个庞杂的诗歌语言系统时,与那种滑过生活和历史表面、依靠素材的丰富性与戏剧性来赢得读者简单触动的类型化写作拉开了距离。在《活页》一诗中,诗人如此描述一艘刚出土的明代沉船:“它黑黝黝的,对天光有点不适应。在思考/造就的黑暗中,它还/没想好怎样向我们开口。”作为读者,面对胡弦的诗歌或许经常会有面对这艘明代沉船般的心情。但幸运的是,尽管一首诗“还没想好怎样向我们开口”,或者说我们还没准备好如何面对一首诗的“开口”,我们依然能够从故事与人事的幽微处捕捉到诗人“在思考/造就的黑暗中”营造出的古朴而新鲜的诗意。 《隋唐嘉话》载:“炀帝凿汴河,自制《水调歌》。”更为人熟知的“水调歌头”则是截取《水调歌》首章演变而成的宋词词牌,该词牌下不乏传世名篇。胡弦以此为诗集题名,深得“水调歌头”另倚新声之要义。在这部诗集中,诗人在复杂的现代世界与斑斓的传统风景之间找到了一个可以从容观看的位置。这种“观看”告别了退守私人一隅的冷眼旁观和耽于古典趣味的玄思静观,以一种介入性的姿态涵容了对这条河流所见证的一切故事、人事的追问与揣度,理解与同情。“所有讲述,都像是对/无法再触碰的讲述的讲述。”“讲述的尽头,是语言/建造的另一座博物馆。”诗也是一种讲述,一种在讲述的尽头重新出发的讲述,它对一再被书写和一再被遗忘的故事、人事一视同仁,它从一条河流的隐喻中捕获了“更宽广的视域和更长久的意义”。在这尽头与出发的交接处,诗人得以清晰地看见:“那是重新被定义的岁月:空气中,/惶恐的信号消失了,/大野恢复了从容的气息。/季节转换,在纤夫的号子和船歌里,/没有迟到者,也没有走得紧迫的光阴。”(《流变,或讲述的尽头》) (李继豪,武汉大学文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诗刊社微信号 | 荐稿编辑:风 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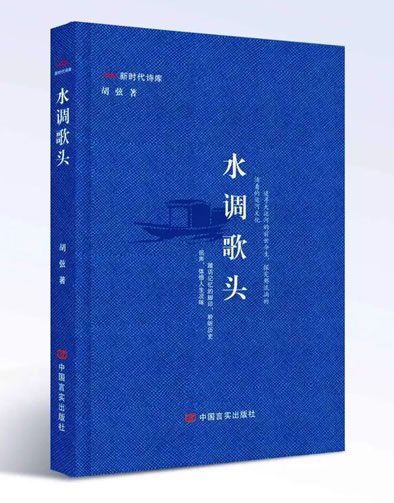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