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禅诗系列理论随笔4-6
——现代禅诗系列理论随笔之4 禅,禅入,禅意,文字般若。 其实,这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是一件事情的不同阶段而已。是一个开始后抵达的过程。 禅本身是一种存在。但这种存在又是那么的独特,像空气,像风,还像水。 它们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被发现,有没有被认识。 空气无处不在,你呼吸,你触摸。但你身在其中,被包含,却又对它几乎忘记。 风是空气的一种运动形式。只有这时,人才能看到它的面目和形体,但它依然是“托物言形”,你看到树木摇曳,尘土飞扬;看到大浪汹涌,乌云翻滚。于是你说,看,那是风,是风在动。它无形,却又有形。有形,却又无形。它不能树立一个永久的标本给你触摸和收藏,所谓“雁穿寒潭,雁过而潭不留影。风过竹林,风去而竹不留声”。它只是在有无之间,给出你一个巨大的想象和意识空间。 水不是空气,但和空气相关,有异处也有共性。水的最大特点是“因物赋形”。它本身从不固执于一种形貌。入于沟渠,便成江河。聚于凹处,便成湖海。遇热升空为雨雾,逢冷落地成冰雪。我想到老子的“上善若水”,以为善应该像水那样,形变而质不变。禅也像水一样,是因机化导的,为召唤迷路者而不惜广开方便之门。 如此,禅便成为一种既可辨又难辨,既能言又无言的存在。 于是,将禅引入文字,犹如引风入林,引水入渠。在正常情景下,树林和沟渠,并不因此被改变,但又真切的与原来不同。它们开始生动,开始有了生命的律动和言说。 禅于诗歌,于写作,我想也是如此。一首诗,一篇散文,引入了禅,于是便改变了内部的结构和气质,有了一种特别的意象和境界,有了一种神秘的生动和空灵。 禅意,当然不是禅,而是嫁接引入后的花朵和果实,但禅意是因禅而生的,这点毫无疑问。禅不在写作者的笔头,只在心中。禅通过写作者的手,渐渐和血液一起注入文字,呈现在文字之内和之外。 佛学中有“文字般若”的说法,一般是指那些翻译优美,深具文学性的佛经典籍,如《金刚经》、《维摩经》等。后来也指那些深含禅意佛理的诗偈文章。般若,智慧也,是对人生对真理拥有的深刻认识和体悟。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写出有禅意的诗歌文章,是否就必须去研读佛教经论或禅语公案?我看未必。既然禅是真理,是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的自然事物,就说明它本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生活里。也就是说,人是天生就具有了佛性的,这也是《金刚经》和《六祖坛经》等禅学著作在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向世人指示的道理。关键是你要发现和认识这真理,要去除遮蔽。 真理不可能被创造,而只能被发现。经论典籍,就是你用于发现的镢头和灯盏,是过河的船筏。它们全是工具,是用于去除遮蔽和黑暗的。我想,一个诗人,一个写作者,若是你自性本明,不被遮蔽,没有迷惑,是用不着这些工具的。只有走夜路的人才需要灯,只有要渡河的人才需要船。 我知道我还需要这些工具,因为我还有许多迷惑,我还常常处在真理的光明之外。但你也许不需要,你心中自性的灯是亮的,你只要认真体味了人生,体味了自然,禅就在了,禅意也就自然而然的在了你的诗歌文章中。 (2006年,成都) 现代禅诗的现代指向 ——现代禅诗系列理论随笔之5 现代,从文字的基本词义上说,是指时间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用到“现代”这个词的时候,一般是指我们身在其中或者是距离不远的一个时代。 但我在这里用到这个词的时候,肯定不仅仅是指时间,而是更多的指向一种艺术的表达方式,或者叫做表现手法也行。我想我这里的“现代”一词,更多的涵义是“现代派”的意思。 我在前面的随笔里已经说到,现代禅诗就是试图用崭新的诗歌表现手法,崭新的语言组合方式,来接通古老禅思中洒脱、反权威、发现自我和无畏追求的心灵自由之路。将禅的意趣智慧,在新的诗歌形式中呈现给世界。 用现代的手法来表现的,当然不再是那些古老的事物。我们既然生活在现代,生活在当下,就只能着眼于当下的生活和感受。思古的幽情可以发,但我们已经回不到古代去了。通往古代的路,是没有商量的永远封闭关死了,我们无法逆时间之河而返。要表达现在的事物,而无视现代的艺术表达方法和技巧,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味仿古,那不但是迂腐可笑,简直就是一种可怜了。复古的游戏只适合自娱自乐,但你要是拿出来当艺术创新来兜售,就成为了一种不负责任的反动和欺世盗名。 一个时代必定有一个时代的语言和书写方式,不然怎么会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的分别和改变?且仔细一看就非常清晰的是,汉语的文字表述形式是在一步步平民化、世俗化的过程中走过来的。到了明清及民国,在文字场上占风头的,就是从民间说书人那里偷来的俚俗故事了,也就是所谓的市井小说。 现代诗歌,或者叫做新诗,在中国满打满算不足百年历史。但可以说,借了翻译之功,我们的现代汉诗基本上已经貌似“国际接轨”了。但这个轨接的似乎还有点儿玄,是那种悬空的危险状态。我们只是学到了一些外在的形式和皮毛,而没有也无法真正深入获取欧美思想和文化中独立、批判的真髓,却又丢弃了中国人文思想中追求独立和自由的那份正统之外的另类传承,于是很多人就只是披了一张现代的皮去招摇过市。 我不反对披这张现代的皮,也不反对招摇,因为这在某种情形下是必要的或必须的。这更是基于内容的改变总是滞后于形式的改变这一普遍规律而发生的。我也时常要披了这张现代的皮走路,但我却还是要理直气壮的反对这张皮下的空洞无物与自夸强大。 在偶然的一个机缘中,我遭遇了禅,于是我选择了将禅和现代诗歌揉合到一块的方法,这就是我今天为之努力探索的现代禅诗。 当我将禅定位为一种心灵的自由追求,一种对自然的向往和回归时;当我将禅定位为一种对自我权利的全新要求和主张,定位为一种对抗权力、专制,对抗阉割人的灵魂的暴行,定位为我的生活样式时,我说,我开始找到了我自己,也明确了我想要的世界和生活。 (2006年,成都) 写诗三境界 ——现代禅诗系列理论随笔之6 借用一下“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修禅三境界。 诗和禅的相通之处,都在一个“悟”字上。修禅要达到至高的境界,是通过修而达到悟。写诗要达到艺术的炉火纯青,也是要通过不断的苦练和探索才能达到。 基本说来,用禅家的修禅三境界,也就是抵达境界高峰的三个阶段,来说明诗歌创作上的三个阶段,也是最为贴切不过的。 第一阶段。开始学诗时,往往是目之所及,情之所动,神之所往,也就是有感而发,将看到听到想到的人事物,诸多现象平端直描出来,唯恐不实不真,唯恐不能言己之志,抒己之情。朴素是朴素了,但在语言文字的锤炼和克制运用上,不得要领,更不要说结构布局上的艺术营造。这时所谓的创作,还只是处在一个原始的临摹状态上,只是将那“山”给非常表像的描画了一下,至于山的蕴藏气质,是一些也没有触到的。这时写作者看到的山,还只是些树木和石头,而不是真正的山。 第二阶段。这样的写作,假如不仅仅是一时半会的青春型冲动,而是作为一种人生的和艺术的长远追求坚持了下来,那么时日即久,便会有一种不满足,有一种想要突破的内心要求。在这种内心强烈的突围意识下,就会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壮举,就会有对于当初那种看山是山的反思和反动。于是,诗作开始出现词语上的华丽绮靡,结构形式上的刻意求奇求新,气势上的风驰雷击,喧天动地。这样的诗,很能给人以激情振奋的感染,对人产生强烈的近距离冲击。并且看上去形满体丰,犹如壮汉少妇,茁健有力。但若认真细观,就还有很多的破绽露出来,不堪挑剔。这个过程,大抵处在“看山不是山”的境界上,是在第一阶段上进了一层,但离真正的艺术高峰,还有一个质的飞跃等在前面。这时写作者笔下的山,是被自己的想象包裹着的山,是云遮雾罩着的山,也就感觉是与以前所见形貌不同的山。 第三阶段。这是一个“繁华历尽,返璞归真”的归依处。人生的风霜雨雪,经历了。生活的咸淡苦辣,尝过了。内心的激情喷涌,内敛了。这时,会有一缕淡淡的怀旧情绪在内心滋长蔓延。对于童年和故乡的回忆,常常成为不变的主题。再看面前的山水,仿佛当年,而不再云烟遍布风雷奔涌了。但这个山仿佛当年,却又明确不是当年。它没有了当年的梦幻多彩,也没有了后来的壮丽高崇。它的一草一木,每块石头,就都是一草一木和一块石头。事实是,山在那里,什么也没有变。变了的是禅者是诗人的心境。这时的写作者会放弃所有的华丽,甚至放弃一切的形容和比喻,而只将山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 如果分行的文字就是诗,如果写这样分行文字的人就是诗人的话,那大多数的诗人将在这看山是山的第一阶段止步。他们只是诗歌的爱好者,是票友,是在一种原始的玩的状态上。接着是那经受住了淘洗的一小部分人,进人到第二阶段。他们在经过了艰难挣扎和选择后,也许会找到一个出口,找到一片自以为适合自己的创造空间,开始自己的经营。但大多也就到此为止了。他们甚至会以功成名就的诗人自居,而实际上也还是作茧自缚,不再有继续突围的力量和勇气。我们在当今所谓诗坛上看到的那群人,就是他们了。能够从第二阶段冲突出来,进入到第三阶段者,少之又少。他们才是化蛹为蝶者,是真正意义上的禅者和诗人。这时,诗歌已经不是写作的事情,而是生命的事情,是哲学和宗教的事情了。一切的追求,这时也都不再是追求。一切的围困,也都不再是围困。这时的诗人已经达到了灵魂的大自由,可以进入“任意随行”的状态了,不再有什么可以成为他身心的障碍。在提笔落笔之间,甚至连禅或诗的念头都不再生起。 冥冥之中,只有一个聚散无定的东西在飘荡,在导引,那便是所谓的禅趣和诗魂。 (2006年,成都) 审稿编辑:云帆沧海 | 责任编辑:风 笛 |
上一篇:医院事故背后的人性与职业操守下一篇:《国富论》:经济与人性的深邃交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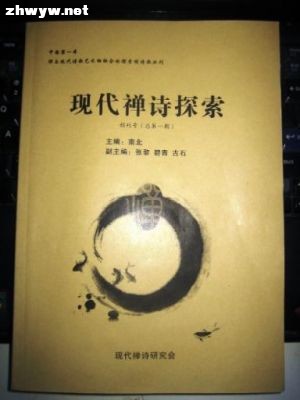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3845号